發布時間:2018-08-01 來源:文匯報 作者:錢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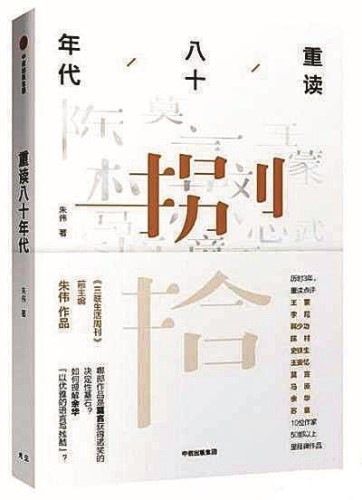
《重讀八十年代》
“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,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;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,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、看世界杯轉播的時代……”這些天,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前主編朱偉寫的這段話,伴隨著他新近出版的《重讀八十年代》,在文學圈屢屢“刷屏”。
講述1980年代文學史的作品有很多。 《重讀八十年代》的不同,在于它是以文學編輯的角度,近距離地、鮮活地重現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現場。蘇童說: “如果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,那朱偉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。”當年在 《人民文學》任編輯的朱偉,曾推出了劉索拉、阿城、莫言、余華、蘇童、格非等一大批作家。
在 《重讀八十年代》中,朱偉系統重讀和點評了十位活躍在文壇的作家的經典。在他的記錄中,作家們“成名前”的寫作風格和之后創作軌跡的變化,文學期刊打破以往條框、力推新人的 “編輯部故事”,都得以一一浮現。有人說,這是一部 “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文學史”,對當年的作家作品有著一份 “親歷者”的體察。而改革開放給文學界帶來的思想、創作風潮的變化,也在他的記錄中留下了清晰的軌跡。朱偉的 “重讀”,也是對改革開放40周年在文學領域的一次有意義的回望。
莫言的成名作是被“逼”出來的,余華最初學的是川端康成
今天我們回顧1980年代,會驚嘆于莫言、余華、蘇童等一大批年輕作家的橫空出世。但倘若真正將時間撥回當初,許多作家的出場,并沒有那么石破天驚。今天在文壇占據中堅地位的很多作家,早期作品的風格頗有些令人意外。而他們創作轉變的契機和軌跡,都在朱偉的這部書中留下了有趣而鮮活的印記。
書中寫到,莫言的成名作 《透明的紅蘿卜》,其實是 “逼”出來的。當年,莫言入選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第一屆學員,同學中最出名的是 《高山下的花環》的作者李存葆。開學后,班上專門開會討論李存葆的新作,在一片贊揚聲中,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調,而且言語中毫不客氣。這個出言不遜的毛頭小子,自然引來了眾人的不滿:只會說別人,自己又能寫出什么呢?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,莫言一口氣寫出了 《透明的紅蘿卜》,他要用一部作品來 “爭一種東西”。
在此之前,莫言只發表過四五個短篇小說,處女作 《春夜雨霏霏》寫的是一位 “軍嫂”向守島部隊的丈夫表達思念之情。用朱偉的話說:“如果只看他剛開始的短篇,會覺得很稚嫩,覺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。”但 《透明的紅蘿卜》1985年發表在 《中國作家》上, “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壇的感覺”。朱偉正是因為這部作品,認準了莫言。在他看來, “還沒有人能將意象表達出這樣一種凹凸感夸張的油畫般的感覺”。在那以后,他騎著自行車一次次趕往魏公村軍藝的宿舍找莫言,之后 《爆炸》 《紅高粱》都是經他之手,在 《人民文學》上發表。
“所以每一個作家都有一個契機,看自己是不是遇到自己合適的寫作方法。”朱偉說。余華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余華最初在 《北京文學》上發表的小說 《星星》,寫的是一個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長過程中的孤獨和憂傷,這篇文章在朱偉看來 “矯情稚嫩”,是一則敘述直白的 “習作”。后來與余華聊天時,他告訴朱偉,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響,因為 《伊豆的舞女》而開始創作,所以走的也是細膩敏感的路子。但在朱偉看來,余華不是一個感覺特別細膩的作家,如果順著川端康成的路子寫,可能一輩子都出不來。直到1986年,讀到卡夫卡的 《鄉村醫生》后,他才如同醍醐灌頂,明白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。這才有了1987年的 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 《四月三日事件》 《一九八六年》,余華脫胎換骨,一躍成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。
從這些 “蛻變”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,思想的解放和活躍,海外文學的大量引進和傳播,對于作家們產生的深刻影響。可以說,正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這些改變,造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學 “黃金時代”。
百花齊放的文學高峰,編輯是幕后英雄
陳村對于 《重讀八十年代》有這樣的 “概括”: “這本書闡述的是作家們如何憑那種被認為很不入流的寫法爬上文壇,編輯處心積慮將作品給鼓搗上版面。”雖是戲謔,卻也道出了重要的事實——當年,許多先鋒的作品并不受到廣泛認可,倘若沒有編輯敏銳的發現力,和力排眾議、打破常規在期刊上推出的勇氣,文學的走向或許會有很大不同。可以說,80年代的文學高峰,與文學期刊、文學編輯們在幕后的推動密不可分。
余華對朱偉有這樣的評價: “在那個時代,他對小說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,他敏銳地發現了一部又一部當時離經叛道現在已成典范的小說。”
1985年,朱偉拿到了劉索拉的《你別無選擇》,這篇大膽的現代派小說讓他讀后直感到熱血僨張。但有人跟他說: “這稿子,你們 《人民文學》肯定發不了。”之前, 《人民文學》主要發表的都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作品,偶有青年作家上頭條,作品也是平穩的現實主義基調。為了力推 《你別無選擇》,朱偉寫了滿滿一頁的稿簽。沒想到的是,當時任 《人民文學》主編的王蒙大力支持,激情澎湃地說,應該突破以往的條條框框,而 “青春的銳氣,活潑的生命,正是我們的向往”!1985年的第三期 《人民文學》將劉索拉的這部處女作用作了頭條,之后又相繼推出了阿城、莫言、馬原等作家的作品,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。可以說, 《你別無選擇》的推出,在1980年代的文壇是一個標桿性的事件,它啟示了后來一系列作家的探索和創新。
舉辦筆會、創作班,也是各刊物培養作家的重要途徑。1982年,朱偉還在 《中國青年》當編輯,參與了期刊在桂林辦的培訓班, “其實就是把人圈起來寫稿子”。他的任務,就是每天和作家溝通創意,給出建議,監督他們創作。陳村就是當年培訓班中的一個,而且是最不羈的一個,他曾屢次與人密謀去外地游玩,都被朱偉斷然阻止。也難怪陳村后來半調侃半認真地說,這種放著好山好水不盡興地玩,關在房間里寫小說的培訓班,之后再也不會參加,“不上當了”。不僅如此,陳村一開始交了一篇應付的文章,但朱偉認為他完全沒有 “用力”, “斃”了以后繼續催逼。正是在這樣的 “逼迫”之下,陳村寫出了 《花狗子嘎利》,后來更名為 《藍旗》,榮獲了多個文學獎項。回過頭來,陳村對這個 “狠心”的監工是服氣的: “朱偉被我們認定是最厲害的文學編輯,是我們的編輯,自己人。”
如今,很多作家回憶朱偉,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。1980年代,他便是騎著這樣一輛車,從一個作家家里,去到另一個作家家里,從相識到相知。正是這輛自行車,串起了他個人的文學履跡,也串起了一張1980年代的文學地圖。它更詮釋了一名文學編輯優秀的理由。今天,我們回望那段輝煌的文學史,在關注那些星光熠熠的作家作品的同時,重新關注那些為文學浪潮推波助瀾的 “幕后英雄”,關注作品的生產、刊發和傳播,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