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23-06-14 來源:安徽作家網(wǎng) 作者:安徽作家網(wǎ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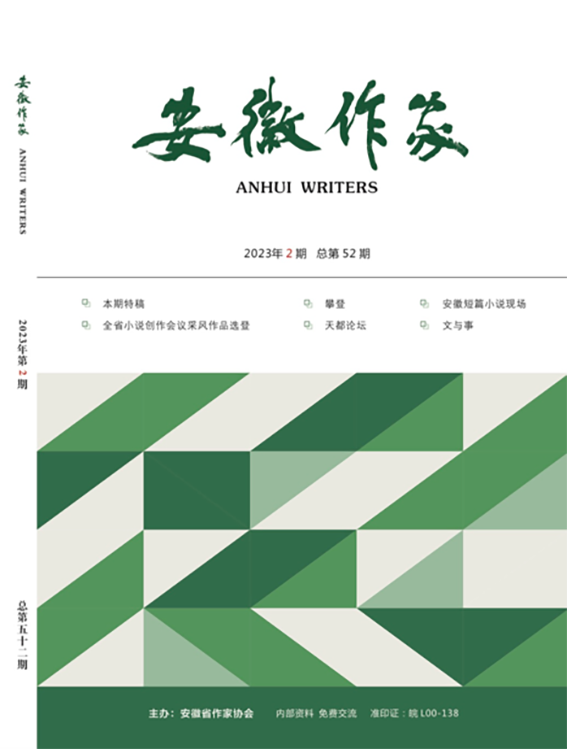
作品欣賞
到河對(duì)岸去
趙豐超
一
我要帶老黃到河對(duì)岸去。
出了院門往西,是一大片彌散著青糠氣的苞谷地,黑壓壓的,比我還高。我事先摸過路,穿過苞谷地里的窄埂,過了西河灘,就能去到淮河邊。我穿著一件父親穿過的、改小了的汗衫,從莊稼地里過一趟,全濕了——苞谷葉子刺撓著我的身子,夜露滋進(jìn)皮膚,熱辣辣的。
我扯著小指粗的牛繩,摸黑往前跑,老黃喘呼呼地跟著。它比我高大,苞谷被它擠兌得噼啪響,我回頭看一眼,白色的沫液在它嘴邊晃成了一個(gè)又一個(gè)圓圈。它已經(jīng)很久沒這樣跑過了。它老了。
前天傍晚,我娘帶三叔來家看過老黃。它本來臥在樹底下,耐心地芻沫,三叔一進(jìn)院子,它嚄地站了起來。三叔拖著腿,圍著它轉(zhuǎn)了一圈,然后對(duì)我娘撇撇嘴,又聳了聳肩膀,像是很失望似的。它真是太瘦了。三叔又去掰它的牙口看,它瞪眼瞅著三叔,鼻孔里呼呼吸氣,好像要從三叔身上嗅出什么來。三叔趿拉著拖鞋,褲子上糊滿了黑乎乎的機(jī)油——他在村口開了一間小店,專門修理拖拉機(jī)。
三叔走后,老黃一直站著,我給它添把草,就去忙別的事了。晚上,我又去給它添草,發(fā)現(xiàn)早先的草還在。它仍然站著。我問娘,娘說青草吃多了嘴苦,抓把鹽給它搓搓舌頭就好了。鹽是現(xiàn)成的,我按娘說的法子,左手攥住它的舌頭,使勁往外拽,右手把合掌的鹽粒子按上去,來回地搓。它的舌頭很粗糙,沒搓幾下就沁出殷殷的血珠子,我趕緊放了手。它甩甩頭,兩個(gè)耳朵像戲偶似的,自動(dòng)朝臉上扇了兩下。我湊近去看,發(fā)現(xiàn)它的眼瞼上濕漉漉的,我以為它是疼的,又問娘,娘說那是害眼病,噴兩口鹽水就好。娘說的肯定沒錯(cuò),很久以前我見父親噴過。在牛身上,鹽是包治百病的。但我沒按娘說的做,我覺得,老黃的病根本不在眼上。
或許它是怵三叔。出門前,我正給老黃飲水。水桶放好,它在桶沿上嗅了嗅,像是嗅到了什么,一轉(zhuǎn)頭,又回到了樹底下。它不吃也不喝。緊接著,院門吱呀一聲被推開,三叔提著一柄比兩個(gè)拳頭加起來還大的鐵錘,悶聲不響地進(jìn)了院子。那是一柄“油錘”,跟三叔身上的那條變了形的勞動(dòng)布褲子一樣,沾滿了機(jī)油。老黃見了錘,打了一個(gè)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響鼻,像是被機(jī)油味嗆著了。
三叔把鐵錘墩在墻根上,自己也蹲了下去。他對(duì)我娘說,大槐樹底下亮堂。他好像很累,多一個(gè)字都不想說。據(jù)我所知,我娘找過他三回,每次他都會(huì)把他的左腿擺出來,擺在桌子或凳子上,翹得高高的——那是一條不能彎曲的腿,顯得比右腿長(zhǎng)一些。自從那條腿出了事,他就轉(zhuǎn)行了。我娘沒說話,忙著給他倒水。三叔給自己點(diǎn)了一根煙,沒喝。我是覷著這個(gè)空檔跑出來的,出門時(shí)三叔吐了一口煙,問我做啥去,我指指老黃說,給它飲水去。
按我的打算,只要到了河邊上,我就把牛繩解掉,把那根一直以來都穿在它鼻孔上的柳樹丫——牛鼻梗也取下來。不管是喝水也好,下河也罷,它都自由了。牛羊之屬,不用學(xué)也會(huì)泅水,我們那兒有“三天牛犢能過江”的說法,老黃生了那么多小牛犢,一條河難不倒它。它一定能泅到河對(duì)岸去的。我聽說,對(duì)岸是一片方圓十幾里的野林子,沒人管沒人問,稗草長(zhǎng)瘋了,滿地都是狗尾巴草。
我從沒去過對(duì)岸,但我猜想,老黃應(yīng)該很喜歡那兒。我回頭看看它,又把牛繩扯得筆直,想讓它快一點(diǎn)。這會(huì)兒,或許我娘和三叔已經(jīng)看出是怎么回事了。可老黃快不了,它實(shí)在跑不動(dòng)了。我只好把繩子松一松,領(lǐng)著它慢慢走。它搖著碩大的肚子,不緊不慢地跟著,顯得很笨拙。我們離對(duì)岸還很遠(yuǎn)很遠(yuǎn)。
天空藍(lán)汪汪的,有月亮,但不是很亮。我又朝村莊的方向看了一眼。月光下,我們的村莊就在堤壩上,高高的,但它的邊界很模糊——多數(shù)人家應(yīng)該都在做晚飯,炊煙和暮靄攪在一起,像淡淡的白米粥。而有的房舍里上了燈,三三兩兩的,不甚光亮,跟螢火蟲差不多。或許,我娘也該做好了晚飯吧。
二
出了苞谷地向西,就是西河灘。
這是一塊坡地,一頭高,一頭低,要從東嶺上放個(gè)倭瓜,會(huì)自動(dòng)滾到淮河邊。我曾在這兒學(xué)會(huì)了翻跟頭和燒豆子,父親的墳就埋在最高的那一頭。
我們緩緩地往下走著,可老黃已經(jīng)三天沒吃東西了,就算是下坡路,它走得也很慢。一路上,它不停地在苞谷、豆秧子上嗅來嗅去。我以為它會(huì)吃一口的,但它只是聞聞。泥土、莊稼,它好像聞不夠似的。它的呼呼哧哧的喘息聲從未停歇。我伸手朝它身上摸了一把,發(fā)現(xiàn)它整個(gè)脊背都是汗涔涔的,有點(diǎn)燙手。它累了,或許它很需要休息。在經(jīng)過父親的墳?zāi)箷r(shí),我本想停下來歇一歇的。可我往來路上望了一下,隱約中似乎聽到一些聲音。我不敢再歇,反而把手里的牛繩又緊了緊。
很快就到了河邊上,一陣微微的河風(fēng)吹來,黏在背脊上的汗衫好涼好涼。
這會(huì)兒的淮河很安靜,微弱的月光照在河面上,水面就像鰱魚的細(xì)鱗,泛著一點(diǎn)點(diǎn)的薄光。河面很寬。往遠(yuǎn)處看,遙遙的河汊子那兒泊著幾條漁船,船上的漁火輕輕地晃著,奄奄一息,或許很快就會(huì)熄滅了吧。對(duì)岸更看不清,一抹淡淡的河霧橫亙?cè)跇溲希蚜肿与吵闪艘粋€(gè)模模糊糊的世界。從這兒看過去,只能看到黑漆漆的林子,林子里到底有什么,誰也看不清楚。
我沖著河面長(zhǎng)出了一口氣。雖然我們慢了一些,總算沒誤事。我把老黃引到河邊上,又撫了撫它的背脊。與我料想的一樣,它仍是不喝水。我本想跟它說些什么的,可時(shí)間緊了些,來不及了。我只能把牛繩一圈一圈盤到手上,臨到嘴跟前,我用手拍了拍它的臉。這幾年,它的皮毛越來越厚,在脖子下面摞成了一堆有著寬厚褶皺的“皮袋”。取牛鼻梗時(shí),它把頭晃了幾晃,皮袋跟著發(fā)出噗噠噗噠的聲響。我順手摸過去,皮袋很柔軟,一層一層,像動(dòng)物的年輪,寬厚的褶皺能容下我的整個(gè)手掌,每一層里都像是塞滿了時(shí)間的秘密。十四年了,它在我們家住滿了十四年。十四歲的我,剛及它的背脊高,可十四歲的它,已垂垂老矣。
我把牛繩跟牛鼻梗都取了下來。老黃自由了,它的身體完全屬于它自己了。我希望它還會(huì)像剛到我們家的那個(gè)晚上一樣——邊叫喚邊尥蹶子,任憑幾個(gè)勞力一起動(dòng)手,也奈何不了它。我朝它屁股上推了一把。河就在眼前,去吧,到河對(duì)面去。我說。
可是老黃沒有動(dòng)。它既不喝水,也不下河,只是眼睜睜地看著對(duì)岸,就跟傻了一樣。我又推它一下,它仍是不動(dòng),它已經(jīng)不是小牛犢了。我有點(diǎn)著急,沖它喝了幾聲,下去呀,下水呀,游過去,到河對(duì)岸去,愛上哪兒上哪兒!我怕它聽不懂,一邊喊一邊用手比畫,還把牛繩揚(yáng)了揚(yáng),提醒它再不走我就要打它了。可它仍然站著,一動(dòng)不動(dòng)。
我已能聽到苞谷葉子的嗶啵聲。他們還是攆上來了。而且,有人很快喊了一聲——在那兒!河谷太空曠了,喊聲漫過我和老黃朝河對(duì)岸滾去,不一會(huì)兒,又滾了回來。就這樣,喊聲在河谷里來回滾著,一下子就把黑夜打破了。
我回頭掃了一眼,影影綽綽的大概有五六個(gè)人,有拿火把的,也有拿電筒的,一窩蜂地從苞谷地里鉆了出來。雖然還隔著一大塊坡地,他們已經(jīng)開始嗷嗷叫,逮到了,逮到了,在那……我真急了,拿盤好的牛繩照著老黃的屁股抽起來,一下,兩下,抽得啪啪直響,快呀,快游過去呀……可它還是沒動(dòng),像是木頭做的——該死的老黃,你究竟在想什么啊?
他們圍了過來。三叔拖著腿慢慢走到我跟前,要奪我手里的牛繩。我不給。他沖我喝了一聲,說,傻不傻?看你娘不收拾你。說完他又來奪繩,我攢足了勁,猛地一揚(yáng)手,把牛繩扔向河心里。三叔給了我一巴掌,很脆響。我回身趴在老黃的肚子上哭起來。它仍在看著對(duì)岸,一動(dòng)也不動(dòng)。
對(duì)岸一片寂靜,河霧越來越濃,樹林慢慢藏了起來,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倒是河心里,月光、星辰,還有火把、電筒,胡亂地照在水面上。牛繩落進(jìn)水里,把一河的星辰都攪碎了。
三
我們又回到了坡地上,老黃走在最前面。現(xiàn)在,它的鼻子上光禿禿的,沒人能再牽它,也沒人去趕它,它是自己走上去的——它像是來看風(fēng)景的,或是聞一聞莊稼和土地,完了掉頭就走。三叔愣乎乎地跟著,我猜,他多少有一點(diǎn)失落。他有好多絕活,但是面對(duì)這樣的老黃,沒有一點(diǎn)用武之地。一拳打到棉花上,他有點(diǎn)泄氣。他說,真沒見過這樣的,不是老迂了吧?我本來在生三叔的氣,這會(huì)兒卻消了,反倒是老黃,我實(shí)在不知道它在想什么,難道它真是老迂了嗎?我對(duì)它好失望。
老黃走了,但它的氣味還在。那根在它鼻子上穿了許多年的牛鼻梗被我緊緊地捏在手里。因泡過油,又被老黃的體液浸潤,現(xiàn)在,它就像一塊玉,不但光滑瑩潤,還沉甸甸的。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砍下這根樹丫的情景——那時(shí)我只有五六歲,我以為他要給我做一個(gè)彈弓。砍好后,他用砂紙打磨了許多遍,這還不夠,他又把樹丫沉到菜油里泡了幾天。我問他,泡油干啥用?他說,浸透了油,再穿進(jìn)老牛的鼻子里,才不會(huì)發(fā)炎。我有些失望,那么好的一根樹丫,竟沒拿來做彈弓。父親一邊捻動(dòng)那根油晃晃的樹丫,一邊說,全家可都指著它呢。我聽不懂他在說什么,也不敢問。父親放下樹丫,背著手朝西河灘去了。
那時(shí)的西河灘還不是莊稼地,而是一片長(zhǎng)滿了燒蓼子和杞柳的河坡。是父親拉著老黃硬把它開成了耕地。燒蓼子好辦,拔幾遍就絕了,杞柳卻扎得深,要先刨去它的根須,才能翻耕土地。那段時(shí)間,父親跟釘耙杠上了,每每刨到天黑之后才回家。他常說,有了這塊地,就能增收兩季莊稼,還愁啥呢?說這話時(shí),他點(diǎn)上煙卷,蹲在牛槽邊吧嗒吧嗒地抽起來。煙絲滋滋地?zé)α艘幌隆?/span>
不久,坡地就平整好了,春天種小麥,秋天種豆子。父親這樣安排。要是我記得不錯(cuò),他應(yīng)該種了十二季,也就是六年時(shí)間。這六年里,我們家確實(shí)好了很多,年年有余糧。可也只是六年。六年之后,父親便管不了了。他在醫(yī)院里住了三個(gè)月,最后被救護(hù)車送了回來。他們說,他應(yīng)該回到家里。父親也同意他們的說法。那天下午,我在給老黃鍘草。娘從救護(hù)車上跳下來,還沒進(jìn)門就開始喊我。我慌亂地跑過去,娘又喊我,叫我趕緊拽一筐稻草鋪到堂屋里。我轉(zhuǎn)頭往外跑,正迎上被抬進(jìn)來的父親。我看到他蠟黃的臉,因?yàn)橥纯喽鴶Q到了一塊。他們把他抬到了草鋪上。在我們那兒,只有將死的人才會(huì)被抬到草鋪上,擺在堂屋的正中間,說是接接地氣,走得順當(dāng)一點(diǎn)。父親在草鋪上躺了三天,第三天的下午他醒了,我要把他抬回到床上,他擺擺手沒同意。那是規(guī)矩,開弓沒有回頭箭,一旦抬到草鋪上,就算一時(shí)半會(huì)兒走不了,也不能再轉(zhuǎn)到床上去。他把我叫到草鋪跟前,幫我把汗衫扣好,對(duì)我說,要像個(gè)大人的樣子。那是他對(duì)我說的最后一句話。我看到,他緩緩地閉上眼睛,五官各歸各位,都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上,他一下子變得很好看……
之后,犁地的事就落到了我頭上。那時(shí)我只有十二歲,整個(gè)夏天,我都架著彈弓在樹林里晃悠。一天下午,我娘把我喊了出來。她先把手按在我的頭頂,量了量我的身高,然后說,你已經(jīng)不小了,可以自己犁地了。我把彈弓揣進(jìn)兜里,仰臉看著她,說,我不會(huì)呀。我娘嘆了口氣,把盤好的牛繩塞給我,說,不用會(huì),你跟著老牛就行了,它會(huì)。我還想再問問,可娘已經(jīng)忙去了。她在幫我準(zhǔn)備東西,牛套、鞭子、犁耙,都是父親用過的……娘幫我把牛套好,又把犁耙搬到拖車上,我還在努力回想父親的樣子,老黃就拉著拖車出發(fā)了。我跟拖車差不多高,不能像父親那樣坐到車梁上,我只能跟在后面跑。
娘說得不錯(cuò),老黃是懂規(guī)矩的。犁地時(shí),它拖著犁在前面慢慢地走,我只需扶住犁桿,跟著它就行。到了地頭上,它會(huì)自動(dòng)停下來,就像等我似的,等我把犁頭調(diào)轉(zhuǎn)方向,等著我繼續(xù)上路。
坡地很曠,一眼望過去,只有地頭上還剩下幾棵杞柳。那時(shí)節(jié)杞柳的葉子正肥,綠油油地?cái)€成了簇簇。老黃沒帶籠頭,臨到地頭上,我以為它會(huì)貪吃柳葉,卻不想它老老實(shí)實(shí)地繞過去了。我甚至連鞭子都沒帶,它就把地犁好了,該走的時(shí)候就走,該停的時(shí)候就停,它對(duì)這塊地太熟悉了。
那是夏天的傍晚,好熱的。犁過半畝地,老黃的嘴角開始淌涎沫,我也累得夠嗆。我留意了位置,待走到杞柳跟前,就把犁頭扎好,原地歇一會(huì)兒。老黃真累了。它站在那兒不住地喘氣,背脊上也是水淋淋的。我得多歇一會(huì)兒。趁著這個(gè)間隙,我開始鼓搗我的小玩意兒——我從河邊摳來一塊黏土,來回摔實(shí),再掐成小坨,摶成一個(gè)個(gè)湯圓似的小球。這是別人教給我的,只要把小球曬干,就能做成圓溜溜的彈子。
這時(shí)候,剛好有幾個(gè)同村的菜戶從集市上回來。他們把船停在離坡地不遠(yuǎn)的碼頭上,推著自行車上了岸。在經(jīng)過我身邊時(shí),我聽到其中一個(gè)人問,這娃子多大了?另一個(gè)人回答說,好像十二了。先前那個(gè)人嘆了口氣,好像很失望的樣子,說,到底還是小孩子呦……那聲音既熟悉又陌生,我癔癥了半天也沒想起那人是誰。我看到,他們上了坡就跨到自行車上,悠悠地朝堤壩上去了。在他們行過的地方,土路被激起一層塵土,久久沒有落下。
坡地上就剩下我一個(gè)人了。那人的話還在我耳邊飄著,也不知為什么,我總覺得那是父親在給我捎話。他為什么要那樣說呢?我不就是小孩子嗎?這時(shí),老黃突然打了一個(gè)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響鼻,像是在叫我一樣。我站起身來,拍拍腿上的泥土,突然想到了父親,想到他蹲在牛槽邊抽煙的樣子。老黃又叫了一聲。于是,我把剛摶好的圓球撿起來,一個(gè)一個(gè)地扔進(jìn)了河里,然后轉(zhuǎn)身朝老黃走去。日頭已經(jīng)下山了,我扶起犁桿沖老黃喊了一聲“起”,這是父親跟它之間的暗號(hào),我見識(shí)過,只要聽了這個(gè)字,它就會(huì)穩(wěn)穩(wěn)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刈咂饋怼@宵S并不欺生,這個(gè)暗號(hào)在我倆之間仍然成立,我話音剛落,它就向前走去。
四
五
三叔終于出場(chǎng)了。最先看到他的,是那個(gè)站在拖拉機(jī)上的人。他一手擎著火把,一手向大伙兒揮動(dòng)。老黃是村里最后一頭牛,他怕大伙兒不知道,錯(cuò)過了什么,竟然扯著嗓子喊起來,都來看哦,都來看殺牛的嘍,再不看,以后可就看不著了。經(jīng)他一喊,廣場(chǎng)上的人真就多了起來,甚至超過了放露天電影時(shí)的觀眾數(shù)量。這幾年,很多人家都買了電視機(jī),按道理說,吃過晚飯他們應(yīng)該窩在家里看電視的。
三叔臉上紅撲撲的,應(yīng)該是喝了不少酒。他手里拖著那柄油乎乎的錘子,一直拖到老槐樹下面。走過圍成一圈的人墻時(shí),大伙兒往后趔了趔,主動(dòng)給他讓出來一條道。三叔并不客氣,挺著肚子往前走,一副大無畏的樣子。
最多也就三百斤肉,多不到哪兒去了。三叔走到我娘跟前,停了一下,他把錘柄靠在大腿上,給自己點(diǎn)了一根煙。在他眼里,老黃已經(jīng)不是一頭牛,而是一堆肉。我娘說,管它多少,沒了它,總能省個(gè)喂它的工吧。三叔猛吸了兩口煙,或許是真喝多了,我覺得他懶懨懨的,連錘子都懶得提起來。我娘又說,難為你了,老三。三叔點(diǎn)點(diǎn)頭,掐滅煙頭,拖著錘,也拖著他的腿,慢慢挪到了老黃跟前。他把錘柄靠在槐樹上,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,然后握緊錘柄,慢慢地舉了起來。
本來說著閑話的人們閉了嘴,他們看著錘子,也看著老黃,廣場(chǎng)上忽然變得很安靜。
有人怕三叔又瞄不準(zhǔn),故意把火把湊近了一些。老黃那紅瑪瑙一樣的眼睛更亮了,就像一面凸面的鏡子。我也湊近了一些,盯著它的眼睛。我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,從它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很多東西——油乎乎的錘子、跳躍的火苗、像老黃一樣安靜的老槐樹,還有排列有序的房舍,以及高矮不一的男女老幼。它每撲閃一下眼瞼,那些畫面就會(huì)自動(dòng)切換一下,我看到,三叔的臉變得好大好大,像一張面盆;我娘把筐挎了起來,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……在老黃的眼睛里,我看到了在場(chǎng)的一切,包括我自己。我的那件對(duì)襟汗衫,已經(jīng)被風(fēng)吹干,顯得大了一號(hào)。再之后,我看到了眼淚,但我不知道那是老黃的還是我的,世界慢慢變得模糊起來。
三叔……這時(shí),我沖著三叔大喊了一聲。
三叔頓了頓,大錘擎在他的頭頂,穩(wěn)住了。大伙兒都朝我這邊看過來,我娘也是。我慢慢把身上的汗衫脫了下來,我覺得,它已經(jīng)足夠遮住老黃的眼睛了。我不想讓它看這個(gè)世界了,我也不想再從它的眼睛里看到什么。我必須把它遮起來。老黃很乖,任憑我把汗衫套到它的頭上,一動(dòng)也不動(dòng)。那件汗衫原本是父親的,現(xiàn)在屬于老黃了。
套完汗衫,我把手掌插進(jìn)了它那寬厚的皮褶,里面暖暖的,很舒服。我真想就這樣睡一覺,在暖暖的褶皺里,一直睡下去。可是,錘子還是落了下去,精確地落到了老黃的額心上。老黃一聲悶哼,原地墩了一個(gè)趔趄,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。
廣場(chǎng)上又熱鬧起來,大伙兒七嘴八舌地說著話。我光著身子,感覺有些冷,我的汗衫已經(jīng)染上殷紅的血跡,沒法穿了。再說,我也沒打算再穿它。在他們圍向老黃的身子時(shí),我沒有聽娘的話,沒有去勾老黃的腿,而是帶著那根被我焐得熱乎乎的牛鼻梗悄悄退出了人群,朝西河灘走去。我不敢再看下去。我聽到他們開始討論牛肉的價(jià)格,有人說要肋條,有人說要牛臉肉。我知道,三叔肯定拿著尖刀開始剝皮了,我娘也沒閑著,她一定握著桿秤呢……
天黑透了,但不是那種啥都看不見的黑,是藍(lán)汪汪的,透明的黑。離火把越遠(yuǎn),世界就越透明。我穿過苞谷地,來到了坡地上。趟過豆秧時(shí),我能聽到豆角炸裂的聲音。然后,我到了父親的墳?zāi)骨啊N铱吹剑谋斏下錆M了斑斑駁駁的鳥屎,灰白相間,像極了碑的瘤子。我本想把那根牛鼻梗埋在父親的墓碑旁,但我突然改了主意,又朝河邊走去。我把它扔到了河里。一聲輕響之后,河面上泛起了圈圈的漣漪,我知道,它一定會(huì)飄到對(duì)岸去的。
夜已經(jīng)很深了,回去的路上,風(fēng)更大了一些,整個(gè)河谷都在發(fā)出刷啦啦的響動(dòng)。經(jīng)過父親的墳?zāi)箷r(shí),我還聽到了老鴰的干燥的叫聲。我突然覺得,萬物蠢蠢欲動(dòng),大地好像活了。
(選自《安徽作家》2023年第2期)
作者簡(jiǎn)介

趙豐超, 魯迅文學(xué)院第三十九屆高研班學(xué)員,安徽文學(xué)院第六屆簽約作家,入選安徽省文聯(lián)“551“青年文藝人才選拔培養(yǎng)計(jì)劃。作品見于《人民文學(xué)》《清明》《青年文學(xué)》《雨花》《天津文學(xué)》《清明》《西湖》等刊。出版有長(zhǎng)篇小說《滾滾淮河》《下一站拉薩》等,其中《滾滾淮河》入選第三屆安徽省長(zhǎng)篇小說精品扶持工程,獲安徽省政府社科獎(jiǎng)(文學(xué)類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