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24-03-19 來(lái)源:安徽作家網(wǎng) 作者:安徽作家網(wǎ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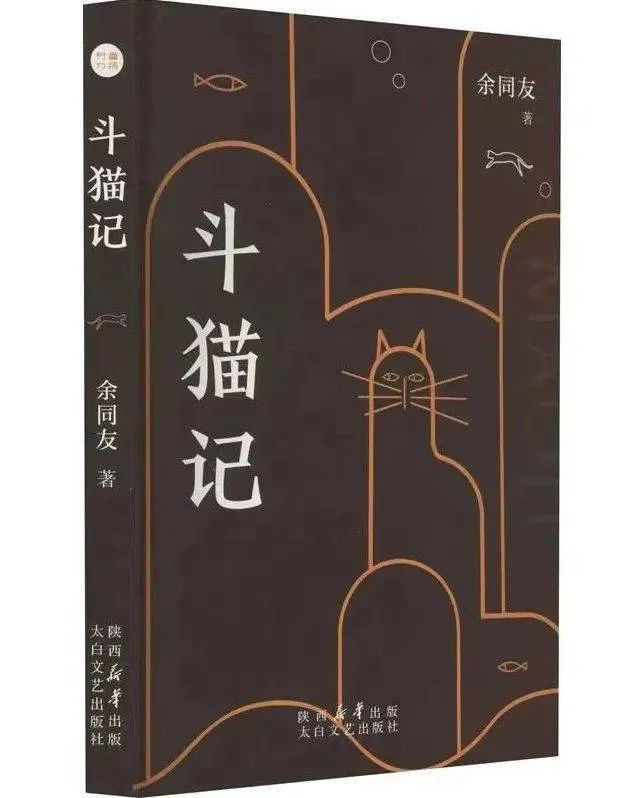
余同友至今已有一百多篇短篇小說(shuō)發(fā)表,可是這位勤奮且又多產(chǎn)的作家,在2018年春天即將到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(shuō)集《去往古代的父親》。此后的五年間,他又有多篇中短篇小說(shuō)發(fā)表在文學(xué)期刊上;除此之外,他還有2部長(zhǎng)篇兒童小說(shuō)、4部長(zhǎng)篇報(bào)告文學(xué)出版;這本剛剛付梓的《斗貓記》,則是他第二部短篇小說(shuō)集。
五年前,我對(duì)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(shuō)集進(jìn)行過(guò)研讀,并寫下了評(píng)論。五年后的今天,當(dāng)我打開(kāi)《斗貓記》,再次閱讀所收錄的14篇小說(shuō)短篇時(shí),覺(jué)察到余同友對(duì)鄉(xiāng)村城鎮(zhèn)化進(jìn)程中所出現(xiàn)的現(xiàn)實(shí)狀況,較之以前有了更為迫切的關(guān)注。這種“迫切”對(duì)于余同友既是被動(dòng)的,也是主動(dòng)的,它有兩種含義:一是當(dāng)下鄉(xiāng)村城鎮(zhèn)化加速推進(jìn)過(guò)程中所呈現(xiàn)出的那個(gè)“迫切”;二是小說(shuō)寫作者余同友感受到了這種“迫切”,并為這種“迫切”所壓。
為了減輕或卸下這種重壓,自皖南鄉(xiāng)村步入城市生活的余同友,幾年來(lái)一次次走進(jìn)皖南與皖西南的許多村莊,“沿著淮河干流走了四省六十多個(gè)縣”,目睹了“淮河兩岸形形色色、大大小小的村莊”(余同友:《短篇小說(shuō)是第一聲鳥鳴——<幸福五幕>創(chuàng)作談》,《紅豆》2019年第7期)中多元且又復(fù)雜的變化后,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說(shuō)寫作有所創(chuàng)意的他,有了不同于過(guò)去的想法。
“想法”是一個(gè)名詞,很抽象,當(dāng)“想法”遵從作家意愿,成為“想辦法”的時(shí)候,就是一個(gè)動(dòng)詞了。在今天,我們誰(shuí)又能生活在現(xiàn)實(shí)之外?我們的作家即使看一看自己所在的社區(qū)居民常駐人口構(gòu)成情況(在很多城市社區(qū),本地戶籍居民常駐人口數(shù)量已明顯小于外來(lái)人口)的變動(dòng),聽(tīng)一聽(tīng)街市上異于這個(gè)城市本籍居民南腔北調(diào)的口音,也能感受到城鄉(xiāng)這兩種人口變量,而帶來(lái)的文化、生態(tài)、經(jīng)濟(jì)、倫理等方面的變化。更何況,隨著城鎮(zhèn)化推進(jìn),原本聚族而居,具有血緣、地緣關(guān)系的鄉(xiāng)村社會(huì),其“人口結(jié)構(gòu)、家庭結(jié)構(gòu)、人際結(jié)構(gòu)不斷的變遷”,實(shí)際上導(dǎo)致了“熟人社會(huì)向‘熟悉的陌生人’社會(huì)的演變”(陳文勝:《城鎮(zhèn)化進(jìn)程中鄉(xiāng)村社會(huì)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遷》,《湖南師范大學(xué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學(xué)報(bào)》2020年第2期)。這樣的“變遷”或“演變”,在鄉(xiāng)村城鎮(zhèn)化未進(jìn)入成熟期之前是巨大的,中國(guó)千百年歷史上從未出現(xiàn)過(guò),它撥動(dòng)著不甘于平庸的作家的心弦,使優(yōu)秀作家難以置身正在衍變的現(xiàn)實(shí)之外,不再滿足以往積累的鄉(xiāng)土文學(xué)寫作經(jīng)驗(yàn),依據(jù)所處的社會(huì)背景,在感覺(jué)方式、思維方式、表達(dá)方式上或各有所創(chuàng)新。
讀余同友的短篇小說(shuō)近作,我有這樣的感覺(jué):這是一位沒(méi)有將當(dāng)下的鄉(xiāng)村與城市分割開(kāi)來(lái)的寫作者。在他的敘事視域中,無(wú)論是皖南山里的“瓦莊”“屏風(fēng)里”“畫坑村”,還是淮河岸邊像“黃臺(tái)子”那樣的村莊,總是與城市(鎮(zhèn))或緊或疏地交織在一起。這種相互交織的程度,因小說(shuō)中必定會(huì)出現(xiàn)的那個(gè)人物的身份、經(jīng)歷、情感不同而各有所不同。余同友就像是站在城鄉(xiāng)尚未彌合地帶的那道狹長(zhǎng)的縫隙中,其小說(shuō)的架構(gòu)、敘事的秩序、情節(jié)的伸延,細(xì)細(xì)品味,大都是在一個(gè)或幾個(gè)城里人的推進(jìn)下展開(kāi)的。如果將這些屬于“城里人”的人物抽離,其小說(shuō)所建構(gòu)的圖景將不再結(jié)實(shí)與完美。
在余同友這些小說(shuō)中我們看到:《幸福五幕》里的王文兵,早已走出村莊、進(jìn)入城市工作與生活,與他的前妻都是大學(xué)的副教授;《丟失的瓦莊》里的“我”和“我”的父親,如今一家人都生活在離家鄉(xiāng)一千公里之外的羅城,多年才回一次瓦莊,也僅是為了給奶奶做八十大壽;而《樹上的男孩》里的張克軍、陳玲玲這對(duì)夫婦,一個(gè)是羅城大學(xué)某學(xué)院帶博士生的研究員、一個(gè)則是有望進(jìn)入大型國(guó)企中層的白領(lǐng);即便《銅錢鐵劍》里的那個(gè)文化程度不高的城市打工者阮和剛,四年才回一次淮河邊的村莊,也只是為了兒子想在城里買的那套商品房要五十萬(wàn),可是還差十萬(wàn),因而他覬覦著仍在鄉(xiāng)下打鐵的父親壓在熔爐磚塊下的——那枚據(jù)說(shuō)價(jià)值十萬(wàn)的“乾隆通寶”銅錢。
凄美的《牧牛圖》更是如此。這篇小說(shuō)以隱晦的筆墨,多次暗示讀者那位從城里來(lái)到“畫坑村”攝影的女人,因?yàn)樘袼氖昵暗牟尻?duì)知青——畫坑村小學(xué)代課老師小張,即便胡家兄弟倆希望是她,但最終也未能確定她是不是當(dāng)年的小張老師。
作為小說(shuō)要素之一的這些“人物”,即便最初的身份是農(nóng)民,或曾經(jīng)在農(nóng)村生活過(guò),但在今天,他們已與“農(nóng)民之間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、進(jìn)行共同的生活或勞動(dòng)”(段成榮:《由“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”向“遷徙中國(guó)”形態(tài)轉(zhuǎn)變業(yè)已形成》,《北京日?qǐng)?bào)·理論周刊》2021年11月29日第14版),他們都在距離鄉(xiāng)村或遠(yuǎn)或近的城市(鎮(zhèn))中生活與工作,事實(shí)上是在城市上班或務(wù)工的城里人。
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認(rèn)為,文學(xué)終歸是“人的文學(xué)”。余同友將這些人的“城市”感知,代入他所敘事的“鄉(xiāng)村”社會(huì),既是他多篇小說(shuō)敘述策略的需要,也是他對(duì)當(dāng)下鄉(xiāng)村城市(鎮(zhèn))化新的文學(xué)理解。他想要寫下的,不再是以往小說(shuō)家敘事中出現(xiàn)的那個(gè)“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”,而是“鄉(xiāng)土中國(guó)”到“城市中國(guó)”這一巨大裂變與彌合期間——那極其復(fù)雜的鄉(xiāng)土社會(huì)現(xiàn)實(shí),并從這些“人物”的個(gè)性出發(fā),藝術(shù)地指向這一特定環(huán)境中人的命運(yùn)與人的生存境遇。
怎樣結(jié)構(gòu)短篇小說(shuō)的情節(jié)與故事,對(duì)于很多小說(shuō)家來(lái)講,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《幸福五幕》中,我看到了余同友的努力。幕開(kāi)幕落,各五次。其中的人物、場(chǎng)景、事件,隨著幕布的拉開(kāi)又落下,我看到了鄉(xiāng)村城鎮(zhèn)化過(guò)程中有些人的幸福與疼痛。這是余同友以戲劇手法精心設(shè)計(jì)并演繹的《幸福五幕》。
《幸福五幕》中出場(chǎng)的人物實(shí)際上只有三位:八歲的王子渙(小學(xué)生),王子渙的父親王文兵(大學(xué)副教授),王文兵的母親王臘梅(黃臺(tái)子整村移民建鎮(zhèn)后的“幸福花園”小區(qū)居民)。韓小蘭雖然也曾在“幸福花園”出現(xiàn)過(guò),但那是前年的事情了,今年春節(jié)之前已與王文兵“辦過(guò)離婚手續(xù),獨(dú)身一人去了澳大利亞”,因而今年回到“幸福花園”陪母親過(guò)年的,只能是王文兵和他的兒子。
《幸福五幕》的故事,是從王子渙好奇地發(fā)現(xiàn)奶奶“半夜起來(lái)趴在床底下念咒語(yǔ)”開(kāi)始的,他覺(jué)得奶奶太像他讀過(guò)的《格林童話》中的“巫婆”了。或許有心的讀者會(huì)注意到,在第四幕中才出現(xiàn)的那只黑陶罐。這只黑陶罐并不是一個(gè)空罐,在這“五幕”劇中,是一個(gè)極為關(guān)鍵的“物的在場(chǎng)”,它所灌裝的“東西”,既是王子渙深夜醒來(lái)時(shí)聞到“一股奇怪氣味”的所在,也是王臘梅能夠暫時(shí)緩解耳朵里那揮之不去的鴨子叫聲的良藥。藏在床底下的“黑陶罐”和那根吸管,猶如經(jīng)典戲劇中的道具及輔助道具,它被余同友打上了追光燈,吸引著父子二人的目光,對(duì)于劇中的人物與觀眾(讀者)就像是一個(gè)隱語(yǔ),在未揭開(kāi)謎底之前,似乎想請(qǐng)他和你都去猜測(cè)一下。
是“迷”的隱語(yǔ),自然會(huì)有人給出“謎底”。揭開(kāi)“謎底”者是王子渙,是王文兵,也是“迷”的隱語(yǔ)制造者王臘梅。
這位“從三十一歲那年丈夫去世,就接過(guò)養(yǎng)鴨的營(yíng)生,一養(yǎng)就養(yǎng)了三十五年”的母親,因淮河行洪區(qū)需要,整個(gè)村莊移民遷住鎮(zhèn)上“幸福花園”小區(qū)時(shí),曾經(jīng)有過(guò)“沒(méi)想到老了老了,我還成了城里人,住上樓房了”的喜悅,但這種喜悅不久便消散殆盡,對(duì)新的生活環(huán)境充滿疏離、陌生、孤獨(dú)感的她,是多么懷念“那些鴨子嘎嘎的叫聲”。況且養(yǎng)鴨曾經(jīng)遠(yuǎn)近聞名的她,還有醫(yī)治鴨子“癱腿”(鴨掌紅腫,站不起來(lái),慢慢就掙扎著倒地而死)的秘方。
這“秘方”、或“謎底”,即是“棉籽油”。它是醫(yī)治鴨子“癱腿”病的絕招,多少年來(lái),王臘梅從不示人,如今就裝在黑陶罐里,那癱腿的鴨子喂上一點(diǎn),病就好了;王臘梅如今吸上一小口,“耳朵里的那些鴨子就不叫了”。
這只黑陶罐簡(jiǎn)直就是一件法器。沒(méi)有它,這篇小說(shuō)將缺乏誘惑力,如果早于第四幕出現(xiàn),這篇小說(shuō)的故事有可能過(guò)于直白,抑或會(huì)失去現(xiàn)在的精彩。
這自然只是我這個(gè)讀者的判斷,但我在“黑陶罐”及罐里的“棉籽油的氣味”中,感受到了作者的智慧。這智慧不同于我們常常要說(shuō)的靈感,它藏匿在少數(shù)作者心里,當(dāng)較為平淡的故事需要時(shí),它會(huì)被“怎么寫”的作家很珍惜的——而且是壓軸式地放進(jìn)小說(shuō)里。
依我之見(jiàn),這“幸福”的“五幕”,其實(shí)自“第一幕”開(kāi)始,那先后出場(chǎng)的人物與道具,就接受了余同友的調(diào)遣,他們不僅進(jìn)入了各自的“角色”,而且經(jīng)過(guò)“五幕”中多個(gè)場(chǎng)次層層遞進(jìn)地表演,都成功地演繹了自己的形象。余同友將這“五幕”劇中的“幸福”與“不幸福”、甚或難以言喻的痛苦,一幕一幕地推演到我們面前。
《臺(tái)上》的故事仍然與淮河有關(guān),而且就在淮河岸邊,但如何去解構(gòu)這篇小說(shuō),余同友卻另辟蹊徑。這篇小說(shuō)開(kāi)頭就有些意思,它摘自《淮河水利手冊(cè)》對(duì)“莊臺(tái)”那不到一百字的說(shuō)明。歷史資料中的文獻(xiàn),放在將要講述的故事之前,本身就具有“元小說(shuō)”因素,它在余同友那里,是不是表明了他所虛構(gòu)的這篇小說(shuō),其故事的真實(shí)性最初始源于歷史中的這類文獻(xiàn)碎片?
《臺(tái)上》是以29個(gè)小時(shí)中8個(gè)確切的時(shí)間節(jié)點(diǎn)為引語(yǔ)(類似本篇小說(shuō)中的小標(biāo)題),并依照時(shí)間的順序來(lái)完成整體敘事的。其敘事軌跡中的場(chǎng)景、情節(jié)、人物,都在29個(gè)小時(shí)(2018年10月13日晚上7點(diǎn)—10月14日夜晚12點(diǎn))中。但余同友筆下的這段時(shí)間,并不止于這封閉的29個(gè)小時(shí),它通過(guò)老范不斷地追述與回憶,獲得了多個(gè)空間的擴(kuò)張與延伸,使“過(guò)去”里的“事件”及“事情”回到了“現(xiàn)在”,這也就很自然地改變了以時(shí)間為順序的線性敘事結(jié)構(gòu)。
在這篇小說(shuō)中,讀者或許會(huì)注意到,這段時(shí)間之外最重大的“事件”是一個(gè)村莊的消失:“二十多年前因淮河治理需要,灘地十年九淹的黃臺(tái)子,成為第一批行洪區(qū)”,整村遷到了“十幾里外的鎮(zhèn)上”;不愿離開(kāi)黃臺(tái)子的老范夫婦,也因此成為留在村莊遺址上的最后兩個(gè)人。而此重大“事件”,在老范眼里,則是二十年后的今天,“與老范未出五服的堂兄弟”——范六三小兒子范團(tuán)結(jié),因犯命案躲藏到他童年生活過(guò)的這個(gè)村莊,于14日夜晚,被追蹤而至的刑警槍擊傷至腿骨,而擒獲歸案。
《臺(tái)上》的故事看上去雖是簡(jiǎn)單,但余同友卻以枝蔓橫生的筆墨,賦予它難以言盡的意味。我們看到,作家是借老范所看所聞、所想所思,敘述黃臺(tái)子的前世今生、興盛和衰落。其中,遷建前“一百四十多口人”擠在黃臺(tái)子“大曬場(chǎng)”上看露天電影的熱鬧場(chǎng)面;老范家不知去向的大黑(狗)與在“別人家老墻上像干部那般散步”的大黃(貓),“嘰嘰咕咕擁擠著鉆進(jìn)雞柵里的雞公雞婆”,林子里默然無(wú)聲地站在樹梢上的烏鴉,傍晚時(shí)分鳴聲響亮飛進(jìn)窩中的鳥雀……等等情景,都在余同友的筆下進(jìn)行了細(xì)微的描述。這種描述無(wú)疑是寫實(shí)的、具象性的,它能夠“立意于象”地使老范這個(gè)人物形象豐滿地站立起來(lái)。
然而余同友似乎并不滿意僅僅這樣的描述,我驚詫地讀到:他借助無(wú)形無(wú)狀虛幻的“風(fēng)”,來(lái)思考人的許多感覺(jué):老范與范六三,因兩家之間的地溝開(kāi)挖位置發(fā)生過(guò)爭(zhēng)吵,“二十年沒(méi)說(shuō)過(guò)話”,但老范目光仍然會(huì)投向他家早無(wú)人間煙火的房子。范六三家的門鎖銹蝕脫落、被風(fēng)吹開(kāi),老范可以“找根鐵絲把門環(huán)穿上把門重新掩上”,但他從沒(méi)進(jìn)去看看。因?yàn)槟枪瘟恕皫装偕锨甑娘L(fēng)”能夠代替他走遍范六三屋子里的每個(gè)角落,而且走在每個(gè)角落的“風(fēng)”聲是不一樣的。房屋本是人類容身之地,意味著家庭成員的歸屬感,但沒(méi)有人住的房子,只能任由“風(fēng)”進(jìn)出。這無(wú)形無(wú)狀的“風(fēng)”,自這篇小說(shuō)的第三章(即“2018年10月14日凌晨3點(diǎn)”)開(kāi)始,竟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刮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個(gè)段落,其用意顯然是借現(xiàn)代主義的意識(shí)流手法,來(lái)描摹老范的心理活動(dòng),使“過(guò)去的歷史”與“當(dāng)下的現(xiàn)實(shí)”重疊在這29個(gè)小時(shí)里。
《丟失的瓦莊》《樹上的男孩》《像一場(chǎng)最高虛構(gòu)的雪》,以及《斗貓記》等短篇小說(shuō),則凸現(xiàn)了余同友感知和表敘這個(gè)世界的另外寫法。在《丟失的瓦莊》中,那個(gè)“我”,是個(gè)虛擬的人物,是余同友借第一人稱進(jìn)行敘事行為的承擔(dān)者,他既是尋找瓦莊這一“事件”的敘說(shuō)者,也是參與者。
令人詭異的是,當(dāng)“我”從遙遠(yuǎn)的羅城乘列車到縣城,再坐中巴車到鎮(zhèn)上后,竟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來(lái)到全然陌生的“前江工業(yè)園”,找不到五里之外去老家的路了。可是上中巴車時(shí),“我”看到車前玻璃上的行車線路明明是“縣城—瓦莊”,但那位售票員和司機(jī)卻告訴他,“從來(lái)沒(méi)有聽(tīng)說(shuō)一個(gè)叫什么瓦莊的地方”。天色將近傍晚,身負(fù)父親之命去瓦莊給奶奶做八十大壽的“我”,想在地圖冊(cè)上找到瓦莊,可是地圖上的“瓦莊”卻變成了“前江工業(yè)園”;更為蹊蹺的是自己身份證上的“瓦莊”、手機(jī)百度上的“瓦莊”,均已消失不見(jiàn)。即使“瓦莊”確實(shí)存在于“我”的回憶中,它此刻已不見(jiàn)蹤影。陷入噩夢(mèng)中的“我”,只能求救于“前江工業(yè)園派出所”民警,但民警卻認(rèn)為瘋顛的“我”可能受到了什么刺激,硬要編造一個(gè)不存在的地方,為了安全起見(jiàn),將“我”約束到翌日天亮,才敢放“我”離開(kāi)。
故事至此尚未結(jié)束。潛隱于敘說(shuō)者背后的作者余同友,將“我”再次扔進(jìn)瓦莊“存在”與“不存在”的悖論中:返回羅城的“我”,在回到家中的那一刻,地圖冊(cè)、手機(jī)百度、身份證上的“瓦莊”竟變了回來(lái);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:在鎮(zhèn)上,原本那個(gè)打不通的村長(zhǎng)老徐電話一撥就通,接過(guò)村長(zhǎng)電話的奶奶埋怨孫子道:撒個(gè)謊都不會(huì),讓她傷心地“等了一天一夜”。沒(méi)有人相信“我”的遭遇,即使“我”的女友李娟也不相信。為了證實(shí)兒子所說(shuō)的遭遇是謊言,父親請(qǐng)完假,竟立即乘動(dòng)車去了瓦莊。
然而幾天后才返回羅城的父親,與“我”經(jīng)歷的遭遇別無(wú)兩樣,故鄉(xiāng)的瓦莊,也被父親弄丟了。而奶奶的電話里的“你騙我,你父親也騙我,你們以后再也不要回來(lái)了”那句話,雖然在父親那里佐證了“我”的遭遇并非是謊言,卻讓傷心的奶奶深陷在兒孫雙重“謊言”的痛苦中。
瓦莊的“存在”與“不存在”,是余同友給敘說(shuō)者“我”設(shè)下的一個(gè)敘事陷阱。這個(gè)敘事陷阱將“我”逼進(jìn)了一個(gè)近乎夢(mèng)魘的境地:只要你離開(kāi)城市,去尋找故鄉(xiāng)時(shí),地名的“瓦莊”便會(huì)消失;只要你離開(kāi)鄉(xiāng)鎮(zhèn),返回“羅城”家中,“瓦莊”這個(gè)地名便又會(huì)莫名其妙地浮現(xiàn)在眼前。讀這篇小說(shuō),或許我們應(yīng)該察覺(jué)到,“我”所敘說(shuō)的故事雖是荒誕不經(jīng),但又隱伏著現(xiàn)實(shí)中的真實(shí),那即是:對(duì)于走出鄉(xiāng)村、已在城市生活了許多年的那些人,今日村莊的向心力、凝聚力,正在日漸衰退,村莊的“丟失”將是他們難以避免的結(jié)局。
與《丟失的瓦莊》比較,《樹上的男孩》和《像一場(chǎng)最高虛構(gòu)的雪》也頗具荒誕性。但前者的荒誕,顯然是在敘說(shuō)者“我”的地理坐標(biāo)轉(zhuǎn)場(chǎng)(從城市到鄉(xiāng)鎮(zhèn),再?gòu)泥l(xiāng)鎮(zhèn)到城市)過(guò)程中才實(shí)現(xiàn)的,而后者的荒誕雖然也與敘事空間轉(zhuǎn)換有關(guān),但并非是直接的因素。
直接的因素是張克軍、陳玲玲這對(duì)夫婦的孩子管管,和“我”的女友父親老吳都是病人:一個(gè)患有自閉癥,必須在臘月二十八就動(dòng)身趕往鄉(xiāng)村的屏風(fēng)里,找到四天前請(qǐng)假回家過(guò)年的保姆蘭姨;因?yàn)檫@些年,保姆換了一個(gè)又一個(gè),唯獨(dú)這位蘭姨孩子能接受,幾年下來(lái),管管已離不開(kāi)蘭姨了,更何況七年前熱戀中的張克軍和陳玲玲以身相許時(shí),便在屏風(fēng)里認(rèn)識(shí)了這位蘭姨。
另一個(gè)則是患有惡性腦瘤,住進(jìn)腫瘤醫(yī)院后,覺(jué)得生命時(shí)日不多,想讓準(zhǔn)女婿的“我”滿足他這一生中最后的酒癮;可是喝過(guò)酒后的老吳便有了醉意,先后竟將“我”當(dāng)成了自己的兩位教師朋友張大橋與許衛(wèi)國(guó),在回光返照中追溯了自己青年時(shí)期與瓦房村姑娘王芳的纏綿情事;更為離奇的是,或許是那一杯酒再次發(fā)生了作用,老吳顛三倒四地又將“我”當(dāng)成了警察,說(shuō)出1986年縣中學(xué)縱火案的秘密:那個(gè)燒死王芳的人就是他自己。
沒(méi)有人愿意自己將來(lái)的岳父是縱火殺人犯,作為準(zhǔn)女婿的“我”,聽(tīng)到老吳這番話,不僅擔(dān)驚害怕,且有了恐懼。這種恐懼感所帶來(lái)的心理障礙,迫使他下意識(shí)地充當(dāng)了“求證”者,找到了與老吳同屆大學(xué)畢業(yè),分配到縣中學(xué)的許衛(wèi)國(guó),以期獲得事實(shí)真相。
荒謬隨之而至。當(dāng)“求證”面對(duì)的不是數(shù)學(xué)幾何證明題,而是與自己有著利害關(guān)系的“案件”時(shí),這個(gè)“求證”者的“我”,竟又讓自己成為了“破案”者。即使這樣的“破案”并非合乎法理。作為讀者,我在這錯(cuò)綜回環(huán)的故事中,再次看到了余同友嫻熟的小說(shuō)敘事技巧:在多條線交織的敘事中,對(duì)人物視角運(yùn)用的重視及別出心裁,這個(gè)“我”,在小說(shuō)作者那里,雖是以第一人稱進(jìn)行敘事,但與《丟失的瓦莊》中的“我”是不一樣的,這個(gè)“我”有名有姓叫小章,在讀者面前,他所講述的故事,并非是自己的經(jīng)歷,均源自老吳、許衛(wèi)國(guó)的回憶,以及“我”的未婚妻吳小越對(duì)父親的印象。
也正是老吳曾經(jīng)最要好的朋友許衛(wèi)國(guó)回憶性的講述,讓1986年縣中學(xué)縱火案水落石出:老吳既不是縱火者,更不是什么殺人犯,“燒死王芳”只是老吳病重回光返照時(shí)一個(gè)荒謬至極的臆想;王芳也沒(méi)死在那場(chǎng)大火中,前些年還回來(lái)參加過(guò)許衛(wèi)國(guó)組織的同學(xué)會(huì)活動(dòng),當(dāng)年她是因?yàn)槔蠀悄懶∨橙酰诶p上自己的那個(gè)小混混的持刀威脅,而沒(méi)有遵守她與他的約定——辭職與她私奔,她只能一個(gè)人傷心欲絕地去了東北,另嫁他人。
因此,這以第一人稱“我”——“小章”所講述的故事,只是對(duì)老吳、許衛(wèi)國(guó)等人所敘之事的復(fù)述。如果從小說(shuō)敘述視角去分析,如此的復(fù)述,雖經(jīng)“我”說(shuō)出,在本質(zhì)上仍是“他說(shuō)”。
但此在的“他說(shuō)”,因?yàn)槭褂昧说谝蝗朔Q,仍然不是全知視角的無(wú)所不知,其所知道的依然是有限的,或然性地露掉了某個(gè)環(huán)節(jié)、某個(gè)真相,那是余同友留給讀者的判斷選擇。比如,縣中學(xué)的那把火到底是誰(shuí)放的?至今仍未明了,交由讀者判斷。
而《樹上的男孩》的敘事方式顯然沒(méi)有這么錯(cuò)綜回環(huán)。患有自閉癥的小男孩管管,由于保姆蘭姨離開(kāi)羅城去了老家屏風(fēng)里,其病癥表現(xiàn)愈加明顯,他自蘭姨離開(kāi)的那一天起,面無(wú)表情,也無(wú)言語(yǔ),整天盯著墻壁上張克軍七年前拍攝的那幅《屏風(fēng)里的春天》,四天沒(méi)吃一口東西。因此,無(wú)可奈何的張克軍決定帶上妻子和兒子,立即動(dòng)身,要把蘭姨追回來(lái)。這便是這個(gè)故事的開(kāi)端。
可故事的結(jié)尾不僅魔幻,而且讓我有了和張克軍、陳玲玲同樣的驚愕:到屏風(fēng)里,管管沒(méi)有見(jiàn)到他們一家人要找的蘭姨,卻一眼看到了《屏風(fēng)里的春天》中的那棵楓楊樹。
這棵樹在這個(gè)時(shí)候出現(xiàn),具有獨(dú)特意義,它不再是風(fēng)景照片上的樹,而是現(xiàn)實(shí)風(fēng)景中的楓楊樹,正是這棵樹由于從二維平面轉(zhuǎn)到了三維立體空間,一下子便戳中了這個(gè)小男孩的心,所以才有了他“一掃平日行動(dòng)遲緩的模樣,跑到溪邊的大樹下,兩腳一縱一縱,那么高的大樹,他竟然一會(huì)兒就爬到了樹端”,坐在樹杈上的管管神情憂郁,像“猴一樣反手搭著額頭,目光望向遠(yuǎn)方”,猶如一個(gè)哲學(xué)家在思考什么。
其實(shí),除了這個(gè)故事的開(kāi)端與結(jié)尾,小說(shuō)中的人物張克軍、陳玲玲、小男孩管管,以及與這三個(gè)人物有所交集的物事,都在那輛小車上——那輛車行駛在羅城到瓦縣屏風(fēng)里的路上。蘭姨雖是這篇小說(shuō)中不可缺少的人物,但她并沒(méi)有在這個(gè)故事中直接出現(xiàn)。張克軍與她的三次相遇:前兩次是在屏風(fēng)里蘭姨家中,后一次是為請(qǐng)一個(gè)好保姆,在家政公司遇到蘭姨,請(qǐng)回家后,沒(méi)想到管管不僅接受了她,而且對(duì)她依賴的程度超過(guò)了他和陳玲玲……這些情景及情節(jié)里的細(xì)節(jié),都是駕車的張克軍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回憶所提供的。
由此而來(lái),這1100公里的路途中張克軍的“回憶”,可以被我視作是這個(gè)故事開(kāi)端與結(jié)局之間的前鋪后墊。這“鋪墊”自這一家人坐進(jìn)車子后,它的兩頭便連接著故事的開(kāi)端與結(jié)局,也連接著吃遍了“各種新藥、特效藥仍不見(jiàn)好”的管管非得去屏風(fēng)里尋找蘭姨的動(dòng)因與結(jié)果。
結(jié)果,在很多時(shí)候,并不是人們想要的那個(gè)答案。因此張克軍聽(tīng)到了樹下陳玲玲那一聲顫栗的尖叫,“危險(xiǎn),管管,你下來(lái)!”可是小男孩從那棵樹上下來(lái)后,陳玲玲又如何去面對(duì)?難道她應(yīng)該譴責(zé)七年前的春天——她和張克軍在屏風(fēng)里熱戀時(shí)的那次激情,而孕育了她和張克軍的孩子?
《樹上的男孩》看上去是以第三人稱進(jìn)行敘事,如果貼近人物與場(chǎng)景仔細(xì)觀察,雖然故事中出現(xiàn)好幾個(gè)人物,但所敘述的焦點(diǎn)始終落在張克軍身上,讀者是能感到以第三人稱所敘說(shuō)的人、物、事,均是張克軍的視角。我之所以再提敘述視角,是因?yàn)樵谶@篇小說(shuō)中,除張克軍外,沒(méi)有別人可以充當(dāng)故事的敘說(shuō)角色,如果換了別人,那將是另一篇小說(shuō)。這其實(shí)是“一種內(nèi)在式焦點(diǎn)敘述,這種第三人稱實(shí)際上已接近于第一人稱敘述了”(童慶炳主編:《文學(xué)理論教程》(修訂版),北京,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8年第2版220頁(yè))。在我看來(lái),這樣去敘述,可以促進(jìn)作者與讀者的相互信任——可靠的敘述者與可靠的讀者。
《斗貓記》實(shí)際上也采用了這樣的敘述角度,其焦點(diǎn)是落在朱為本身上的,是第三人稱敘事視角的變形。我們看到:闖入朱為本視野的,首先是那只貓,一只懷孕的白貓。會(huì)做凍米糖的朱為本,算是瓦莊的一個(gè)能人,當(dāng)他心事重重走進(jìn)自家院子,瞧見(jiàn)這只“肚皮快拖到地上的”白貓時(shí),故事中所有的人物:老伴王翠花、孫子朱小森、賣泥鰍的王德勝、鎮(zhèn)上糕點(diǎn)店的老板以及準(zhǔn)備回家過(guò)年的兒子兒媳,先后都與他及他憎惡的那只“模樣怪異”的貓,發(fā)生了縱橫交錯(cuò)的聯(lián)系;更為重要的是:在人與貓的這場(chǎng)戰(zhàn)爭(zhēng)中,那只懷孕的白貓,由于老伴和孫子的善待,面對(duì)朱為本的喝斥、腳踹、吹火筒趕、竹竿捅、彈弓打,總有辦法與他從容地周旋,就是賴他家里不走,這便成了朱為本的噩夢(mèng)。
可是朱為本又不能將他憎恨這只貓的真正原因說(shuō)出來(lái)。這是一個(gè)必須窩在朱為本心里的秘密。這個(gè)秘密自朱為本從市醫(yī)療機(jī)構(gòu)拿到后,便藏在他的口袋里,不能讓任何人知曉,因?yàn)樗麩o(wú)法面對(duì)村里人的議論“這孩子像他媽”的言外之意。那張紙他看了一遍又一遍,就是不敢將紙上的內(nèi)容告訴在外打工的兒子,更不敢告訴去年因高血壓輕微中風(fēng)過(guò)的老伴王翠花。有意味的是,作者余同友在這篇小說(shuō)即將進(jìn)入尾聲時(shí),才借朱為本的視角,道出這張紙的秘密即是“親子關(guān)系鑒定報(bào)告”。試問(wèn)之,在瓦莊、或瓦莊這樣的鄉(xiāng)村,有誰(shuí)能接受自己的兒子、孫子,不是血親意義上的親兒子、親孫子?如果老伴與兒子知道了這張紙的存在,朱為本這個(gè)家的“天就塌下來(lái)”了。這張“親子關(guān)系鑒定報(bào)告書”,是小說(shuō)家余同友對(duì)筆下的情節(jié)、背景、人物(也包括那只貓)的設(shè)定,它既是人與貓之間戰(zhàn)爭(zhēng)的根源,也是導(dǎo)火索,朱為本正因?yàn)檫@張紙的存在,才讓他覺(jué)得兒媳“丁秀麗的臉長(zhǎng)得和那只來(lái)歷不明的貓?zhí)貏e像”,從而導(dǎo)致了他那不可理喻的怪誕行為。也許我們能從這張很輕又很沉重的紙上,看到倫理失序、道德滑坡的現(xiàn)象還在今日城鄉(xiāng)彌合期間的社會(huì)上演,朱為本和他一家人的遭遇,也僅僅是這個(gè)時(shí)期的一點(diǎn)投影而已。
我們還是來(lái)看看小說(shuō)是怎么結(jié)尾的吧:值得慶幸的是,噩夢(mèng)中醒來(lái)的朱為本,將拌進(jìn)“毒鼠強(qiáng)”的“那盤香噴噴的干泥鰍”扔進(jìn)了灶膛里,因?yàn)樗麆倓倝?mèng)見(jiàn)老伴和朱小森因誤食干泥鰍,口吐白沫倒在地上。其時(shí),王翠花已領(lǐng)著朱小森來(lái)到院門前,那“爺爺!爺爺!”歡快的叫聲,讓他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應(yīng)對(duì)。而屋頂上的那只盤腿而坐的白貓,此刻已經(jīng)不見(jiàn)蹤影。那只貓好像比朱為本更詭譎、更聰明,是它終止了這場(chǎng)戰(zhàn)爭(zhēng),讓焦慮的朱為本再無(wú)事可做,只能像那只貓一樣,喉嚨里發(fā)出“喵嗚——喵嗚——”的叫聲。
可是,我們從朱為本這貓一樣的叫聲里,并沒(méi)感到他和他們這樣的“戰(zhàn)爭(zhēng)”,就此能結(jié)束。
這也是此篇小說(shuō)作者余同友給我們的提醒及示意。
在余同友的短篇小說(shuō)中,《牧牛圖》有可能是一個(gè)特例。這些年,我陸陸續(xù)續(xù)讀過(guò)他的五十多個(gè)短篇,卻從沒(méi)讀到他以如此靜寂的方式去敘說(shuō)一場(chǎng)雪。
這場(chǎng)大雪,仿佛給余同友打開(kāi)了一個(gè)新的寫作空間,我看見(jiàn),他所架構(gòu)的這個(gè)小說(shuō)文本圖式,由于是建立在風(fēng)景如畫的“畫坑村”地基上,便不再像他多個(gè)短篇中所顯現(xiàn)的那樣——在結(jié)構(gòu)上波詭云譎般的復(fù)雜,在敘事中所漫溢出的荒誕及語(yǔ)言的詼諧,其敘事走向及故事中的情節(jié),清晰得猶如被畫坑村山里的大雪照亮。
《牧牛圖》如泣如訴所敘說(shuō)的故事是疼痛的,主要人物胡芋藤的性格形成及他兄弟倆的結(jié)局雖是凄涼至極,但在余同友那干濕濃淡相宜相輔的筆觸中,仍讓我讀到了中國(guó)畫筆墨里所帶來(lái)的那種美學(xué)意境,即便那是一種冷抒情背后的凄清凜冽之美。
我在《牧牛圖》中看到:當(dāng)那個(gè)女人“抱著一架黑色炮筒樣的照相機(jī)”,走到胡芋藤、胡芋苗身邊時(shí),哥哥胡芋藤就覺(jué)得她像當(dāng)年的上山下鄉(xiāng)知青——在村小學(xué)代課的老師小張。四十年過(guò)去了,胡芋藤的記憶依然清亮:他20歲那年給小張?zhí)敉晁愤^(guò)教室時(shí)見(jiàn)小張老師不在,放下水桶走進(jìn)教室,在黑板上寫下了“張老師您好”五個(gè)字,后來(lái)有人告訴他,小張老師說(shuō)“這字寫得不錯(cuò)”。也正是小張老師的夸獎(jiǎng),讓只“念了三年書”便輟學(xué)務(wù)農(nóng)的胡芋藤,對(duì)模樣好看、說(shuō)話京腔京調(diào)好聽(tīng)的這位姑娘生出愛(ài)慕之情。然而這只是他單方面的情絲,除了“字寫得不錯(cuò)”那句話外,他即使再努力,也沒(méi)引起小張老師的注意,更別說(shuō)得到小張老師的青睞或親近。
在胡芋苗眼里,能讓哥哥與小張老師彼此體膚貼近的,是那個(gè)“下雨天,山洪暴發(fā),公路沖斷”,讓站在河邊立即想“趕回城去看生病母親”的小張老師急得哭了起來(lái)。胡芋苗趕來(lái)時(shí),見(jiàn)哥哥背起小張老師已摸索在湍急的河水中,直到“洪水退過(guò)后的第三天,累癱的他才回到家中。”自此,“哥哥的腿出了問(wèn)題”,幾個(gè)月后一條腿壞死被鋸掉,剩下的那一條好腿,也在四十年后的今天,“開(kāi)始跟他過(guò)不去”,常常痛得他欲死不能,只能痛苦地活在這個(gè)世界上。可是哥哥即使知道小張老師那次離開(kāi)后,再也沒(méi)有回到畫坑村的真實(shí)原因,其實(shí)是“急著去縣里辦回城手續(xù)”,也從沒(méi)怨恨過(guò)她。
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與我一樣,有這樣的感覺(jué):這場(chǎng)大雪是余同友給這個(gè)短篇定下的一個(gè)基調(diào),它流露了作者書寫此篇小說(shuō)時(shí)的思想感情與寫作態(tài)度,如果不圍繞這場(chǎng)大雪,小說(shuō)敘事的構(gòu)成將流于結(jié)構(gòu)的表層,因?yàn)槟且彩呛筇佟⒑竺缧值軅z所盼望的大雪。在《牧牛圖》中我們見(jiàn)到:來(lái)到畫坑村攝影的那個(gè)女人,答應(yīng)過(guò)兄弟倆,“這里的景色我拍得差不多了,下次我就冬天來(lái),下第一場(chǎng)雪的時(shí)候我一定來(lái),我估計(jì)冬季的雪景應(yīng)該是不錯(cuò)的。”顯而易見(jiàn),從這句話中,我們就可以知曉:等待“冬季雪景”來(lái)臨,再次面對(duì)相機(jī)鏡頭表演的兄弟倆,實(shí)際上是在等待那個(gè)像小張老師的女人到來(lái)。那張出自這個(gè)女人之手,獲“國(guó)際大獎(jiǎng)”的攝影作品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(diǎn):它就放在兄弟倆房間里,“面朝著胡芋藤的床,看到這幅相片,胡芋藤那難以忍受的腿痛就好像減輕了一些”。
那張裝進(jìn)像框的大照片無(wú)疑是美麗的:因?yàn)樵凇拜p煙漠漠、白鷺斜飛、老牛慢走、垂楊吐綠”的水田景色映襯下,兄弟倆曾按照那個(gè)女人的要求,“穿蓑衣戴斗笠”,弟弟犁田、哥哥放牛,細(xì)雨打在他倆那“暗含喜悅”之情的臉上,宛如一幅水墨勾染的“春耕牧牛圖”。
但這種喜悅只保留在相片上。為了等待在“冬季雪景”中的表演,兄弟倆在冬天到來(lái)之后,雪還沒(méi)落下來(lái)的時(shí)候,便穿戴好蓑衣與斗笠,趕著牛拉著犁,在畫坑村的土地上進(jìn)行著表演之前的預(yù)演。那場(chǎng)大雪終于落下來(lái),而且是“一連下了三天”,兄弟倆也在雪地里演了三天,仍然沒(méi)有等到那個(gè)想拍攝“雪中牧牛圖”的女人到來(lái)。
這第三天的夜晚,將兆示這個(gè)悲劇的結(jié)果:筋疲力盡的兄弟倆晚飯也沒(méi)做,都倒在了床上。天將黎明時(shí)分,當(dāng)胡芋苗聽(tīng)到因疼痛而咬著筷子的哥哥在喊著他的名字,要他“幫幫我!幫幫我!”的時(shí)候,夢(mèng)中驚醒的弟弟,看見(jiàn)哥哥竟然和那個(gè)面色兇惡的女人廝打起來(lái),他“拿起一個(gè)枕頭往那個(gè)女人臉上悶去”,直到那個(gè)女人再無(wú)動(dòng)靜。放下枕頭的胡芋苗,這時(shí)才有點(diǎn)清醒,覺(jué)得不對(duì)勁,拉亮電燈,并不見(jiàn)那個(gè)女人,那個(gè)被他悶在枕頭下是哥哥,已在自己的眼前死去。
在我看來(lái),這個(gè)女人是不是當(dāng)年的小張老師,似乎小說(shuō)作者也不愿意說(shuō)破,余同友好像是有意識(shí)地不給讀者標(biāo)準(zhǔn)答案。我們只能從四十年前后——小張老師和那個(gè)女人同樣夸獎(jiǎng)胡芋藤“字寫得不錯(cuò)”這句話,以及“那個(gè)女人的臉”在兄弟倆眼里“還真有幾分像”小張老師,去猜測(cè)那個(gè)女人有可能是小張老師。然而這“可能”中又有著“不可能”,因?yàn)楹筇僭鴨?wèn)過(guò)那個(gè)女人是不是姓張、是不是當(dāng)過(guò)老師的時(shí)候,那個(gè)女人詫異地回答道,“是啊,我就是姓張,你們?cè)趺粗牢倚諒埬兀坎贿^(guò)”。她說(shuō)完“不過(guò)”這兩個(gè)字之后,便無(wú)下文。從這個(gè)句子的語(yǔ)法來(lái)分析,連詞“不過(guò)”是對(duì)前面那個(gè)句子的轉(zhuǎn)折,后半句話雖然沒(méi)說(shuō)出來(lái),但可以認(rèn)為在肯定自己是姓張之后,卻又是對(duì)“當(dāng)過(guò)老師”的否定,只是她覺(jué)得沒(méi)有必要向一個(gè)被拍攝對(duì)象說(shuō)出后面的話而已。
如果認(rèn)真審視,當(dāng)下的短篇小說(shuō)寫作是處于邊緣地帶的。許多小說(shuō)家放下了他們?cè)?jīng)熱愛(ài)的短篇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,轉(zhuǎn)而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的創(chuàng)作中。這自然是傳媒與批評(píng)界市場(chǎng)運(yùn)作的結(jié)果。
在此環(huán)境下,哪位作家還能一如既往熱愛(ài)他的短篇小說(shuō),尤顯珍貴。這也是我多年來(lái)持續(xù)注目余同友短篇小說(shuō)創(chuàng)作的緣由。這回再次評(píng)論他的短篇小說(shuō)近作,是我繼五年前對(duì)他第一部短篇小說(shuō)集進(jìn)行評(píng)論之后的再次文學(xué)追蹤,它表明了我心之所想:期待有更多人去閱讀他的短篇小說(shuō)。
【作者簡(jiǎn)介】楊四海,中國(guó)作協(xié)會(huì)員,在《散文》《散文選刊·選刊版》《長(zhǎng)江文藝》《文藝報(bào)》等發(fā)表作品;出版有散文集《河邊敘述者》等三種。作品被收入《21世紀(jì)中國(guó)最佳散文(2000-2011)》《中國(guó)隨筆年度佳作2011》《新散文百人百篇》《零距離?名家筆下的靈性文字》等多種選本;散文集《河邊敘述者》獲湖北省第九屆文藝楚天獎(jiǎng)文學(xué)作品類特等獎(jiǎng);多篇散文曾分別獲得湖北省文藝楚天獎(jiǎng)文學(xué)獎(jiǎng)、《安徽文學(xué)》年度散文獎(jiǎng)、長(zhǎng)江文聯(lián)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成就獎(jiǎng)等。
轉(zhuǎn)自:安慶文藝評(píng)論微信公眾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