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(fā)布時間:2023-06-20 來源:安徽作家網(wǎng) 作者:安徽作家網(wǎ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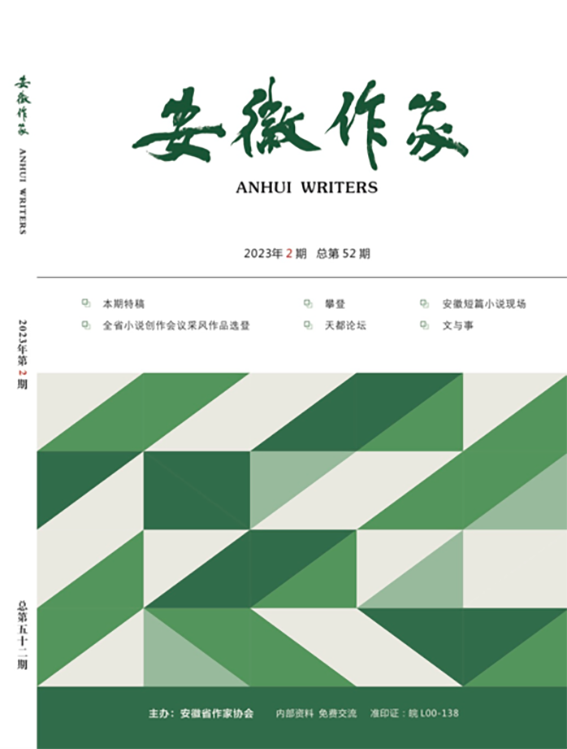
作品欣賞
春天里的舞影
朱斌峰
春天里的夜晚有神秘女子驚現(xiàn)而舞的消息,是彩山村村長打電話告訴我的。當(dāng)時,我正在銀城玻璃制品公司展廳里,領(lǐng)著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,觀賞九層玻璃塔的模型。村長的聲音從大山深處飄來,遲遲疑疑,像是被風(fēng)吹得欲斷還續(xù)的細(xì)線。我禮貌地掐斷電話,心生煩躁。我早已不再關(guān)注新聞、八卦和流言——有人歡欣鼓舞地說這是偉大的信息時代,可在我眼里,那些紛紛擾擾的信息無非是不同面目的裁縫各取所需縫制的盛裝,看似天衣無縫,其實(shí)破綻百出,甚至衣不遮體。我有個號稱影視界大咖的朋友祥子,三杯酒下肚,就會激情洋溢地說起當(dāng)紅明星的秘聞,如同親眼所見,其實(shí)只是在販賣不知從哪兒聽來的緋聞——不過那家伙搖晃大腦瓜的樣兒,像是為大燈泡做廣告,還是可親可愛的。我不奢望從那些滿天飛的泡沫里聽到真相,只是耐心地保持著微笑,就像面對一堆碎玻璃發(fā)出的聲兒——可村長的消息還是讓我心里飛進(jìn)了半只蜜蜂。
春天里不是季節(jié)的名稱,而是一幢立在山谷里的房子。去年,我從彩山村村民手里買下兩塊宅基地,花了比制作微型玻璃塔還要長的時間,建起了那幢玻璃房。不大的山谷里只有它遺世獨(dú)立著,鋼木結(jié)構(gòu)的三層樓,大面積的玻璃墻收集著山巒、云朵和星星的影子。山谷外的彩山村,徽派舊宅和水泥小樓錯雜著,墻根下的木風(fēng)車、田野里的稻秸垛、大樹下坐著的戴草帽老人,顯得空曠而寂寥。那幢玻璃房就像是從我心里長出來的,唯一遺憾的是,每逢雷雨天,房內(nèi)的電閘就會被閃電嚇得兀自跳開——據(jù)說源源不斷的電流從城里抵達(dá)山谷就已微弱,只有插上兩根水泥桿安上變壓器,才能保持玻璃房燈火通明。我原本想把它建成民宿,可建成后就不愿對外開放了。我偶爾會獨(dú)自或約上三五好友去那兒,跟山風(fēng)、樹林、飛鳥作伴,過幾日不被打擾的時光。
有天晚上,我獨(dú)坐在陽臺上,看著天上的星星。手機(jī)里有人在唱《春天里》,不知是汪峰還是旭日陽剛。我聽了一遍又一遍,聽得眼睛都濕了,于是就把玻璃房命名為“春天里”。
我不愿意有陌生人走進(jìn)春天里,即便那是個神秘的會跳舞的女人。
春天里的確住著一個女人——她叫梅姐,是個幫我打理玻璃房的五十多歲的胖婦人。
梅姐一直跟隨著我,在春天里還沒影兒時,她是銀都玻璃制品公司的廚娘。我愛吃她燒的酸菜魚,百吃不厭。更早之前,我還沒出生時,她就跟她家的桃樹以鄰家姐姐的姿勢,站在我家隔壁的院里。礦山家屬區(qū)有著排列成行的平房群,像是被酒醉的詩人寫亂了的詩行。我家所在的那行詩句里,住著九戶人家,外墻都是紅磚的,內(nèi)墻刷著半截綠漆,每家每戶格局相似,都擺放著木頭茶幾、五屜櫥、黑白電視機(jī)什么的。夜半時分,礦區(qū)地皮輕輕顫動時,我就覺得自己正乘坐著一列綠皮火車,在大山里鉆來鉆去。礦山工人來自五湖四海,口音相雜,像是奔赴同一個目的地的旅客,可每個人的來路不同,什么金沙江、葫蘆島、楓香墩,那些陌生的地名讓我好奇而又向往。梅姐的父親來自四川,從部隊(duì)轉(zhuǎn)業(yè)到礦山大食堂當(dāng)炊事員。他總把白毛巾搭在肩上,隨時隨地擦著臉上的汗。他愛搖晃著胖墩墩的身子,臉上漾開滿足的笑,吹噓他在部隊(duì)是神槍手,吹噓他老家有座石佛有大山那么高,吹噓他的廚藝全礦第一,渾身得意勁兒仿佛礦上人都是他喂養(yǎng)的。梅姐卻是安靜的,她站在她家的桃樹下,眼神像是被天上的小鳥叼走了。
每每吃晚飯時,梅姐會隔著竹籬笆,遞給我一小碗酸菜魚,像是給饞嘴的小貓喂食。
我吞下魚片,仰著臉問她,梅姐,你長大后想做什么呀?
她甩甩長頭發(fā),能干什么?做礦工唄!我真想去銀城,做紡織廠女工。
我嘻笑,大頭哥說,紡織廠女工多,鋼鐵廠男工多,最好男去紡織廠女進(jìn)鋼鐵廠。
她咬著米粒,為什么啊?
我盯著她好看的臉,物以稀為貴嘛……那樣就好找對象了!
她的手指從竹籬笆穿過來,點(diǎn)在我的頭上,你啊,真是人小鬼大!
其實(shí),那時我們早就覺得有些事情是天生注定的,當(dāng)南腔北調(diào)的父輩來到大山里建起礦山后,他們就坐上了同一列火車。作為他們的兒女,我們會子承父業(yè)把礦工進(jìn)行到底,只不過男生大多下井采礦,女生可以去礦山廣播站、幼兒園、地磅房、礦燈房而已。我們已經(jīng)撇去父輩的方言,以同樣的腔調(diào)說話,就像兄弟姐妹一樣有著同樣的命運(yùn)了。我們曉得礦工是自豪的職業(yè),卻想去大山外的銀城上班——雖然礦區(qū)有學(xué)校、糧站、郵電所、衛(wèi)生院、供銷社、工人俱樂部,足夠讓我們衣食無憂地完成娶妻生子、生老病死,卻沒有像銀城那樣的動物園。我們常常擠上運(yùn)送礦石的小火車,在哦哦哦的汽笛中,在咔咔咔的微顫中,鉆出大山去往并不遠(yuǎn)的小城,而紡織廠、冶煉廠、鋼鐵廠就是銀城的標(biāo)記。
我偶爾能聽見梅姐在院子里輕輕哼著歌兒,跟芭蕾舞里的小天鵝似的轉(zhuǎn)著圈兒,哼著轉(zhuǎn)著,那棵桃樹就開花了,她就長大了。
從礦山技校畢業(yè)后,梅姐果然去地磅房上班了。沒過多久,她就有了男朋友。那家伙是礦山附近制藥廠的銷售員,高高大大,頭發(fā)自然卷,腰上的鑰匙串發(fā)出叮叮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慕饘俾暋?jù)說他很有本事,制藥廠的葡萄糖一半是他賣出去的。他第一次走進(jìn)隔壁院落時,我就對他有著莫名的敵意,就像面對突然而至的闖入者。
我隔著竹籬笆,賭氣似的對梅姐說,梅姐,我不喜歡卷毛哥!
梅姐有些意外,為什么呀?他有啥不好嗎?
我悶聲,反正就是不喜歡他!
梅姐咯咯地笑了。
梅姐嫁給卷毛哥后,常常坐在卷毛哥的摩托車后座上,風(fēng)馳電掣地回來吃飯。卷毛哥能吹牛會喝酒,總跟梅叔喝得勾肩搭背親如兄弟。梅姐就像偷食了梅叔的面包發(fā)酵粉幸福地胖了起來,連笑聲都胖了。
就在梅姐生下女兒時,礦山因資源枯竭關(guān)停了,那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,如同發(fā)生了一場火車脫軌側(cè)翻事故。運(yùn)礦小火車停開了,工人俱樂部聽不見《咱們工人有力量》男聲大合唱了,機(jī)關(guān)大樓樓頂大喇叭啞了,礦工們紛紛下崗出外尋生計了,人去樓空的礦區(qū)恍惚一下子就衰老了。梅姐下崗后,長頭發(fā)剪成雞窩狀,整日抱著女兒在臺球室里忙碌著,臉色蠟黃了。我在心里問自己,為什么梅姐不能像礦上的廣播員——那個從北京來的單身阿姨那樣,躲過時光的腐蝕,總保持著小姑娘的樣子呢?
那時,我在銀城東奔西突,先開了玻璃店,為小城千家萬戶切割玻璃門窗、安裝玻璃陽臺,然后又在開發(fā)區(qū)的田野上拿下一塊地,建起玻璃制品廠,生產(chǎn)盛裝化妝品、藥品、酒水的器皿。等稍稍能喘口氣時,我回到礦區(qū),才發(fā)現(xiàn)梅姐正在破敗的街道上枯萎著。卷發(fā)哥跟一個長發(fā)女人好上了,梅姐跟那女人明爭暗斗后離婚了,正帶著女兒靠著臺球室過生活。她灰頭灰臉,整日神情慌張,臉上像是銹住了。她還患上了一個毛病,一看見女人的長發(fā)就會心悸眩暈發(fā)偏頭痛,那應(yīng)該是婚姻事故留下的后遺癥。于是,我將梅姐母女接到銀都玻璃制品廠。她不愿意跟玻璃打交道,就一直在廠里做廚娘,燒的酸菜魚還是當(dāng)年的味道。
這樣的梅姐真沒什么神秘的。
我不相信春天里有人夜半而舞,可傳言還是像無微不至的風(fēng)來了。
我想我應(yīng)該去彩山村堵住村長的嘴,讓那流言不要傳開。我開著車捎著朋友祥子,從銀城向大山駛?cè)ィ皇侨ゴ禾炖铮侨グ菰L村長。我想了許久,也沒想出村長向我透露傳聞有何居心,只是想起他曾熱情地陪我逛過整個村子。他指點(diǎn)著村里的舊祠堂、半山的寺廟、遠(yuǎn)處的雞鳴驛和空置的徽派舊宅,說起當(dāng)?shù)氐恼乒剩勂鹚氚巡噬酱褰ǔ捎耙暸臄z基地的計劃,并懇請城里大老板的我為他出謀劃策牽線搭橋,當(dāng)時我滿口應(yīng)承了——也許村長是在提醒和催促我吧。我邀請祥子同行,就是想讓他以影視界資深人士的身份,考察考察彩山村,給村長一個交待。我甚至想,如若村長肯緘口不語,我愿意為美好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制作一個應(yīng)景的玻璃雕塑。我在車上把事兒跟祥子說了,祥子摸著被安全帶勒緊的肚子,彌勒佛般眉飛色舞起來。
這算啥事?你一個大老板,怎么還為這種小事嘰嘰歪歪?
我呵呵地笑。
其實(shí)咱倆挺有緣的……我以前在國營燈泡廠干過……吹過玻璃燈泡兒。
哦?
那時,咱們廠長牛皮哄哄,整天說要造出人造小太陽!
人造小太陽?
就是那種一千瓦的氙氣燈……廠長想用那種大燈泡照亮光明路整條街。
那廠長的計劃成功了嗎?
沒有!咱們是狗咬豬尿泡空熱情了一場……當(dāng)年咱們真是年輕啊!
后來呢?
后來,燈泡廠被廠長買斷成了私營企業(yè),專門生產(chǎn)霓虹燈了。
……
我不知道祥子的故事是他親身的經(jīng)歷,還是他習(xí)慣性的虛構(gòu),也許連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。我很佩服祥子能把每一個故事,說得生龍活現(xiàn),說得津津有味。我在建成玻璃制品廠時,也曾有過生產(chǎn)玻璃燈飾的想法,連名字都想好了——三色照明公司。可我只會收集液體,不會收集光,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銀都廣場上建起高聳的九層玻璃塔,與小城銅質(zhì)鐘樓、木構(gòu)鼓樓遙相呼應(yīng)。
山路越來越窄越彎曲,植被越來越多越充沛。我們漸漸把喧囂拋在身后,遁入靜靜的時光。我們鉆到彩山村時,村長已經(jīng)在村部門口迎候了。大山被濕濕的綠浸潤著,山頂縈繞著白白的霧氣,天上的云里似乎藏著一場細(xì)細(xì)的雨水。我們跟著村長走走停停,那個外表墩實(shí)的中年男人把村里的掌故又講了一遍,說得那么熟稔,就像吐著一根被日光暴曬過的稻草。我聽得懨懨欲睡,只是意外地發(fā)現(xiàn)村頭曬稻場多了個名叫彩山人家的小型民俗博物館。那石基土墻的大院里,擺放著水缸石磨、風(fēng)車?yán)珑f、織布機(jī)繡花鞋、木制搖籃和銅鎖扣上的木柜之類的器物,在昏黃的光線里彌漫著遙遠(yuǎn)的告別氣息。祥子發(fā)出夸張的笑聲,不停地用手機(jī)取景拍照,似乎想把那些老物件收進(jìn)手機(jī)里。我知道要不了多久,我的朋友會在朋友圈里,以九宮格長篇累牘地推出做舊了的照片,引得點(diǎn)贊如蜜蜂般嗡嗡飛起。
等我們在村部坐下,偌大的會議室里只有祥子洪亮的聲音了。那個大嗓門的家伙滔滔不絕地說起影視圈見聞,高屋建瓴地談起彩山村打造影視基地的策略,信誓旦旦地說他可以引進(jìn)他的朋友執(zhí)導(dǎo)的《山鄉(xiāng)巨變》劇組走進(jìn)彩山村。他的話就像泥石流沖刷而來,村長插不上嘴卻蠢蠢欲動著,不停地斟茶遞煙點(diǎn)頭稱好。我知道祥子的話滿是水分,聽著聽著卻忍不住激動起來,既然喬家大院、宏村染坊能憑著一部影視劇火起來,那彩山村未必不能如祥子所說聲名鵲起的。一陣風(fēng)從窗外吹來,我倏地冷醒過來,為自己剛才的激動羞愧。其實(shí),我并不想彩山村被人打擾,可那些激動人心的話讓我中蠱了——也許我們都是叫不醒的做夢人。
奇怪的是,村長一直沒有提春天里有人跳舞的事兒,那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幻聽了——作為曾被玻璃的尖嘴刺傷過耳朵的人,偶爾幻聽是不無可能的。可等我們坐進(jìn)鄉(xiāng)村土菜館,喝得耳酣面熱的村長竟然開口了。他說好多村人都看見過,午夜的玻璃房陽臺上,有個長發(fā)女子穿著白色衣裙跳起舞來,待細(xì)看時又不見了。我雖然早有心理準(zhǔn)備,可仍聽得心驚肉跳,仿佛那是個不祥之兆。
我喃喃,怎么會?怎么可能有這種事?
村長篤定地看著我,怎么說呢?咱們這兒有個傳說……聽說很久很久以前,彩山上就有白云變成女子在山頂上跳舞……咱們的先人就是看見那個異象,才在這兒定居下來開花散枝的。
我心稍安,這個傳說聽起來還算吉利。
村長的臉被酒泡得模糊了。后來就總有人看見白衣女人跳舞……就說四十年前吧,一個從上海下放到村里小學(xué)教書的女子跳下懸崖后,又有人看見白衣女子在山上跳舞……沒想到這事兒又在您的玻璃房出現(xiàn)了……
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,嘴上浮出笑,怎么會?不科學(xué)嘛!無稽之談!
村長連聲應(yīng),對對!就是個無根無據(jù)的傳說!
一串笑聲潑染開來,祥子腆著大肚子眉開眼笑了,這是好事啊!不管這事是有是無,只要傳開來就能吸引人來……有些景區(qū)不就是編造這樣的噱頭吸引人氣么?看來這里就要成為網(wǎng)紅打卡地了!
我和村長怔怔地看著祥子那張過于肥大的臉,都沒說出話來。
我恍惚聽見春天里滿山谷的鳥雀聒噪起來。
關(guān)于春天里的傳聞,就跟龍卷風(fēng)般流傳開了。
先是祥子發(fā)了朋友圈,繪聲繪色地說起彩山村一個玻璃房里疑似出現(xiàn)了靈異事件,還配發(fā)了一張嫦娥奔月的圖片。接著,好幾個熟識的朋友打來電話,或開玩笑或神叨叨地向我查證傳聞的真?zhèn)巍N沂缚诜裾J(rèn),卻讓他們更信以為真了。再后來,傳言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傳開,不時有陌生人打電話給我,說要入住春天里民宿,氣得我差點(diǎn)換手機(jī)卡了。果然,流言比瘟疫還有傳染性,比風(fēng)跑得還要快。我討厭流言蜚語的灰塵,卻不怨祥子,他真正的身份是小城作家,就是靠販賣浮光掠影的故事為生的——至少他比那些拼貼新聞販賣消息的媒體工作者要有趣。我沒答理這事兒,不信一條虛假的小魚能翻起浪花。我想要不了多久,這條傳聞就會被更多的泡沫淹沒,就會煙消云散。
事情總是出人意料:竟然有人根據(jù)流言判斷我在春天里金屋藏嬌了,懷疑跳舞的長發(fā)女子是我的情人。她是睡在我身邊的女人,眉毛畫得很細(xì),眉峰畫得很高,很重的眼影遮不住眼角的皺紋,臉部就跟懸崖峭壁似的。她沒有跟我爭吵,在我面前總是冷著臉專心致志地涂著腳指甲,私下里卻派人在玻璃房前蹲守,仿佛那條流言變成銹跡斑斑的釘子扎進(jìn)她心里了。我想跟她解釋什么,卻不知怎樣開口,又不敢把事兒越描越黑。我寧愿她在春天里捉到跳舞的女人,是聊齋里的狐貍也好,是我的情人也罷,那樣她懸著的心也許會踏實(shí)下來。我甚至想雇一個長發(fā)女人去玻璃房跳上一曲午夜的孔雀舞,了卻她的心愿。
我更沒想到春天里因傳言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。梅姐急急地打來電話說,她發(fā)現(xiàn)一到夜晚就會有好多眼睛甚至攝像機(jī)鏡頭對著玻璃房,讓她提心吊膽,像是囚在大探照燈下的監(jiān)房里——這真是讓人不愉快的感覺,城里已經(jīng)有足夠多的電子眼了,為什么大山里還要有復(fù)眼動物呢?我思來想去,不便派保安去守護(hù)玻璃房,只好單身赴會去往春天里。
這天晚上,我吃過酸菜魚,與梅姐坐在玻璃房陽臺上,喝著咖啡閑聊。晚霞逐漸散去,天空和玻璃墻顯出純凈的暗藍(lán),山谷里的樹林在風(fēng)中輕輕搖擺。
我問梅姐,你看見過有女子穿著白衣,在陽臺上跳舞嗎?
她搖搖頭,斑白的短發(fā)像被秋霜打過。
我又問,那你相信那個傳聞嗎?
她還是搖頭。
我輕輕地笑,那你怕什么?
她抬起眼,慌慌地掃了掃四周的樹林,我不怕鬼怪,就怕人的眼睛。
我看見她哆嗦了一下,便低下聲,梅姐,別怕!沒什么可怕的!
她定定地看著我,點(diǎn)了點(diǎn)頭。
我倆又說起礦山往事,聊起她遠(yuǎn)在北方上大學(xué)的女兒,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聲音跟山風(fēng)融在了一起。漸漸,那種久遠(yuǎn)的好看的笑,從她的臉上漫了出來。
等星星出來偷聽時,我倆各自回臥室了。不知梅姐有沒有安然入睡,而我在靜等著午夜的到來。我一遍遍地摩挲強(qiáng)光手電筒和一把角鐵制成的刀,那不是為可能出現(xiàn)的白衣女子準(zhǔn)備的,而是用來對付那些窺視玻璃房的眼睛們。我要看看那是些什么樣的人,必要時將刀插入他們的臀部。我從小就明白刀是雕琢事物最干凈利索的器具——我曾用那把刀嚇跑過少年時的情敵,討要過玻璃工程款——只是那把刀有些生銹了。我對自己用刀的準(zhǔn)確性充滿自信,懂得如何把刀恰如其分地插入人體部位。我要重拾舊刀,制造一樁流血事件,把那些眼睛從春天里趕走。
當(dāng)指針指向午夜十二點(diǎn)時,我拎著強(qiáng)光手電筒和刀,踅出玻璃房,鉆進(jìn)樹林里搜索起來。幾道強(qiáng)光暴射之后,傳出幾聲驚呼,然后強(qiáng)光和驚叫就被黑色吞沒了。我繞著山谷走了一圈,看到了九張被強(qiáng)光手電筒照射得驟然變形的面孔。有六個陌生人自稱是喜歡探險的驢友、直播愛好者和新聞從業(yè)人,那些葉公好龍、鸚鵡學(xué)舌的家伙膽子真小,被我嚇得丟下一臺小DV和半截手指落荒而逃了。
還有三人是熟人,我不得不把他們請進(jìn)玻璃房里。
我盯著一張熟臉,你是村長,怎么也在這里蹲守呢?
村長抹抹頭上的汗,舌頭打結(jié),那個……你別誤會,我只是想搞好平安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哦。
我又轉(zhuǎn)向另一張臉,祥兄,你呢?
祥子腆著坦坦蕩蕩的肚子,我嘛,就是想親身體驗(yàn)一下,創(chuàng)作一部《午夜驚魂》之類的電影!
我笑笑,看向旁邊抖抖索索的人,那個高顴骨的年輕男人仍閉著眼,像是被強(qiáng)光手電筒照瞎了。我沒問他什么,他就是被人派來捕捉我的情人的人。
梅姐沒有走出她的臥室,也許她睡得太熟,沒有什么能驚醒她。
梅姐是自愿來春天里的。她說她總失眠,就想找一個安安靜靜的地兒,也許那樣就能睡好覺。我起初不同意,擔(dān)心她一個人在山谷里太孤單太不安全,準(zhǔn)備找個當(dāng)?shù)卮鍕D打理玻璃房。她就一連幾天都不燒酸菜魚,執(zhí)拗地表示她生氣了。我只好答應(yīng)下來,真希望山谷里的風(fēng)、云和星星能治好她的偏頭痛。
梅姐第一次偏頭痛發(fā)作,可能是在警車帶走我的那天黃昏。之前的某個夜晚,剛上礦山技校的我和三個小伙伴,去銀城翻進(jìn)鋼鐵廠倉庫拿了些角鐵,用技校實(shí)訓(xùn)車床制成刀的形狀,又跟冶金技校的學(xué)生打了一架,用那角鐵制成的刀刺破了冶煉廠子弟的大腿,于是公安就找來了。他們開著警車奔來,把我們從礦山技校里揪了出來,游街示眾般帶著我們緩緩駛過礦區(qū),以威懾我們的同類。當(dāng)警燈閃爍的警車嗚啦啦地駛向地磅房時,我把臉貼在車窗上,看見了站在青磚地磅房前的梅姐。她看見我,捂著嘴尖叫一聲,愣了愣,就邊喊著我的小名邊跟著警車跑起來。她跑著跑著,腳步飄搖,忽地捂著腦瓜坐在柏油馬路上——后來我才知道她犯了偏頭痛。我起初以為是警車的叫聲讓梅姐落下病根的,后來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冤枉了公安——在我認(rèn)識的公安朋友中也有患偏頭痛的——也許有些人就像天生潔癖一樣,對某種聲音過于敏感吧。我從看守所放出后,被父親暴打一頓,在家里關(guān)了一個多月。我蝸在天昏地暗的家里,耳朵變得越來越靈,一聽見隔壁傳來小鹿般的腳步聲,就走到竹籬笆前,對著下班歸來的梅姐笑。梅姐會停下腳步,甩甩長頭發(fā)跟我說說話兒。她不無憂慮地說,你啊你,這樣混下去,礦里是不會收你當(dāng)工人的,你長大后怎么辦呀?我只能摸摸發(fā)青的頭皮暗自氣餒,臉上卻堅持著嘻笑。那時工人是光榮的職業(yè),而不能成為國家正式工、集體工就是盲流——現(xiàn)在想來,梅姐的擔(dān)憂是多余的。
我第二次看見梅姐犯偏頭痛,是在礦區(qū)工人俱樂部前。那天早晨,街上飄著淡淡的霧氣。卷毛哥像一粒臺球從臺球室里滾出,騎上摩托捎著長發(fā)女子揚(yáng)長而去。梅姐從臺球室里沖出,看著摩托長發(fā)飄飄而去,癱倒在水泥地上號啕起來。我上前去扶她,發(fā)現(xiàn)她像是散了骨架,怎么也扶不起來。霧氣越來越淡,圍觀的礦工家屬漸漸多了。我情急之下,背起梅姐一溜煙地跑回家。梅姐的偏頭痛嚴(yán)重地發(fā)作了,痛得出現(xiàn)了幻覺,說她看見長發(fā)在她眼前飄來飄去,要我把那長發(fā)快快剪掉。我找到剪刀卻找不到長發(fā),心知那旗幟般的長發(fā)已被摩托帶走了。梅姐悲泣地訴說著,說她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丈夫,真是命苦。梅叔叉著腰氣洶洶地對著空氣罵,說他要是有槍就一槍斃了卷毛狗。梅嬸唉聲嘆氣,說男怕入錯行、女怕嫁錯郎,女兒怎么嫁了個吃喝嫖賭的男人呢!我沒有說話,轉(zhuǎn)身回臥室用砂紙磨打起角鐵制成的刀。
一天晚上,我在迪斯科舞廳找到卷毛哥。那時,他從制藥廠停薪留職,下海辦了那家黑燈瞎火的舞廳。我對舞廳并不陌生,知道那里無非有一些男女在幽暗的燈光下,借著跳交誼舞的幌子,摟摟抱抱摸摸捏捏而已——我曾在那兒的地板上踩到過已經(jīng)使用過的避孕套。我也曾在舞廳經(jīng)理室,獨(dú)自翻看過卷毛哥偷偷從香港弄來的《龍虎豹》,那畫報上的裸女讓我熱血沸騰。
我一走進(jìn)舞廳經(jīng)理室,卷毛哥就笑著迎過來,像往常一樣拍拍我的頭,小弟,你咋來了?
我盯著他,梅姐那么好,你為什么還搞外遇?
他臉上肌肉僵了僵,聲音是軟的,這個……你還小,不懂。
我冷笑,懂你媽!說著刀就跳了出來,插在他的大腿上。
他痛呼一聲,趔趄地跌坐在沙發(fā)上。
門被嘭地撞開,一個看場子的光頭沖進(jìn)來抓住我,對著卷毛哥喊,老大,你沒事吧?是做了這小子,還是把他交給公安?
卷毛哥擠著眉頭,揮揮手:放他走。
光頭愣了愣,手慢慢松開了。
卷毛哥看著我,小弟……那種事,長大后你就懂了……你走吧。
我犟犟脖子,上前撿起刀,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轉(zhuǎn)身而去。
很多年后,我偶遇早已成為電子廠門衛(wèi)的卷毛哥,想上前握握他的手卻忍住了。我說:卷毛哥,作為男人我懂你了,可我不能原諒你!卷毛哥訥訥,唔,為啥?我笑笑,有時我連自己都不能原諒!卷毛哥沒再說什么,像個陌生人轉(zhuǎn)過身子。我眼睛有些潮,發(fā)現(xiàn)曾經(jīng)高大帥氣的卷毛哥過早地佝僂了。
梅姐的偏頭痛最后一次嚴(yán)重發(fā)作,可能是在聽到梅叔亡故的那天。那時,她正在銀都玻璃制品公司食堂燒酸菜魚,鼓搗起騰騰的熱氣。一個電話打來,有人告知她梅叔在鄉(xiāng)村到礦區(qū)的路上,掉進(jìn)河里淹死了。沒了礦山大食堂,日漸衰老的梅叔偶爾會去礦區(qū)四周的鄉(xiāng)村,為村里人家紅白喜事幫幫廚,然后紅光滿面地騎著自行車回家。他老人家應(yīng)該是喝酒喝多了,騎車栽進(jìn)那條礦山排污河里的。我聞訊趕到食堂,看見一只翻蓋手機(jī)斷了翅膀似的扔在一邊。梅姐正抱著頭蜷縮在地上,在喊,痛!痛!痛啊——而酸菜魚的香氣正在四處彌漫。
其實(shí),我對春天里能養(yǎng)好梅姐與生俱來的暗疾,是沒有信心的。
春天里午夜舞女的傳聞,就這樣沒造成實(shí)質(zhì)性影響,泡沫般消散了。
有個朋友曾推著鼻梁上的深度眼鏡,憂心忡忡地勸誡我,這是現(xiàn)象即本質(zhì)的時代,傳聞會變成真相。你必須消除那個流言,否則那流言傳久了就會成為事實(shí)。我覺得他的話是囈語,可還是心悸了許久。當(dāng)春天里恢復(fù)平靜后,我在心里竊笑眼鏡朋友,無論什么時代,謊言都不會變成金條——人想得太多就會生病哦。我剛放下心來,祥子打來電話,壓低大嗓門神秘兮兮地說,春天里的舞女,只會在月圓之夜出現(xiàn)。我一笑置之,沒把這話往心里去。我很忙,得在銀城人模狗樣地活著,要用玻璃吹制漂亮的器皿,甚至制造透明的玻璃塔——春天里的玻璃房只是我的偷閑處而已。
天近中秋,月亮圓了起來。我想起自己好久沒去春天里了,就開著車迎著黃昏的落日,甩掉銀城向大山駛?cè)ァR淮贝备邩堑牟A粔ν巳ィ蛔嗌畹纳綆n圍來,我恍惚鉆進(jìn)時光的隧道。車至彩山村,我忽然想起祥子的話,心里一動閃出個念頭:月圓之夜,玻璃房的陽臺上究竟會不會出現(xiàn)白衣舞女呢?于是,我停下車在鄉(xiāng)村土菜館吃過晚飯后,悄手悄腳地攀上山谷里的石巖,眺望起玻璃房。身邊的樹木野草青潤欲滴,仿佛叮叮咚咚的泉水就是從那些樹根葉脈里流出來的。山頂薄云濡上微濕的青色,漸漸跟月光融成一片。對面玻璃房里,燈火不知何時亮起,又不知何時熄去,只留下陽臺上那盞明晃晃的大燈。我沒有看見梅姐的身影,只看見月光在玻璃墻上無聲地紛落。
我左顧右盼,等著午夜的降臨。我早已經(jīng)歷過一次次焦急的等待,可這次卻有著悠然的清閑,就像把自己泡進(jìn)了慢放的時光里。我恍惚聽見草叢里的蟲鳴、樹葉的呼吸,看到夜氣下植物在悄悄枯榮,感到一縷縷涼意沿著大腿游了上來。
月亮升上山巔,果然又圓又亮。忽而,對面玻璃房的大燈驟然雪亮,我睜大眼睛,真的看見一個白衣女子出現(xiàn)在陽臺上,甩動長發(fā)跳起舞來。她仰著臉看著圓月,雙手上舉,腳尖踮起在悠悠轉(zhuǎn)動,就像抓住長發(fā)要向月亮飄去。我用力揉揉眼睛,就在那女子轉(zhuǎn)過身時,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那張臉是屬于梅姐的。她的臉被月光照得很白很白,白得沒有一絲皺紋。我在心里深深地喊了聲梅姐,卻不敢驚動她,悄悄轉(zhuǎn)身踅出山谷,在山下啟動汽車悄無聲息地駛上月光的軌道。
春天里漸漸遠(yuǎn)去,我確定自己沒有喝酒,也沒有產(chǎn)生幻覺。我在心里問自己,我怎么從沒發(fā)現(xiàn)梅姐喜歡跳舞啊?梅姐的短發(fā)怎么會變成長發(fā)呢?難道她買了頭套?難道是我看花了眼?
車至銀城,我才打開車載音樂,一首歌像料峭的風(fēng)撲面而來:如果有一天 我老無所依/請把我留在 在那時光里/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離去/請把我埋在 這春天里——
我想我該為春天里種上一樹桃花了。
作者簡介

朱斌峰,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,魯迅文學(xué)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第32屆學(xué)員,安徽文學(xué)院第四屆簽約作家。曾于《鐘山》《青年文學(xué)》《安徽文學(xué)》《西湖》《雨花》《青春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《黃河文學(xué)》等發(fā)表小說,被《中篇小說選刊》《長江文藝·好小說選刊》《作品與爭鳴》選載。獲2015年《安徽文學(xué)》年度文學(xué)獎小說獎、第二屆魯彥周文學(xué)獎提名(優(yōu)秀)獎,參與編劇的廣播劇獲全國第十二屆精神文明建設(shè)“五個一工程”獎。